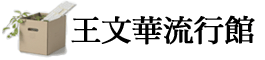■
如果我得了癌症…… •王文華
最近最喜歡的英文字,是「Companionship」。
「Companionship」是從「Companion」來的。「Companion」,是「同伴」,「Companionship」,我叫做「陪伴」。
最好的陪伴,當然來自家人和愛人。但若沒有愛人,來自朋友也好。當我年紀越來越大,愛人越來越少時,我在朋友身上,找到陪伴。
這些朋友大部分是女的,比我大五到十歲,有的單身、有的離婚。我們之間沒有男女的浪漫,或性的緊張。和她們在一起我自然,和她們在一起,我有安全感。
她們是我可以臨時約吃飯的人,回國後第一個打電話的人,心神俱疲時想講話的人,遇到好女孩第一個帶去炫耀的人。
年輕時,我不覺得男人和女人可以做純朋友。這想法,是被經典愛情片《當哈利碰到莎莉》害的。片中哈利(比利克里斯多)第一天遇到莎莉(梅格萊恩),就勾引她上床,因為他堅信男人總想跟他喜歡的女人上床,所以男女之間不可能有純友誼。五年後他再遇到莎莉,稍稍修正了自己的理論,但也好不到哪去:「男女不可能成為朋友,除非他們已各自有了愛人。等一下,就算這樣也不可能。因為你的愛人會無法瞭解為什麼你有了他還需要別的朋友,是不是你們的愛情少了什麼!」
這是我大學時代的電影。哈利的理論在大學時聽起來那麼有道理,是因為我們的確都希望喜歡的女生變成女友。也許我們沒那麼急著上床,但基本上那是奮鬥的方向。為達目的,我們會用一大堆拐彎抹角的方法,比如說跟你們班聯誼啦、邀你來參加我們校慶啦、跟你做學伴啦、認你當乾妹啦、和你家族聚會啦、你失戀時安慰你啦、借你複印筆記啦、和你談法國電影啦、幫你介紹家教啦、鼓勵你追尋夢想啦……唉,族繁不及備載、招數亙古如一。但不管表面上裝得多麼清高、距離保持地多麼巧妙,內心深處,我們還是想牽你的手、掀你的裙角。
大學雖然畢業,愛情的觀念卻繼續留級。一直到30歲,和女人的關係都是非白即黑。在那性幻想豐富、想像力卻貧乏的年紀,男人和女人的可能性少得可憐。像英文動詞,男女之間要嘛就是現在式、要嘛就是過去式、不然就是未來式。現在式打得火熱、未來式緊追不捨、過去式都是豬哥。很少人分手後還會聯絡,一旦發現追不到就轉移目標。「我愛你」和「我恨你」這兩句話,有時只有一個月的距離。原因是當我們說任一句時,並不真懂它的意義。
在這樣線性發展、邏輯簡單的男女關係中,上床就像舞台劇的謝幕,是最快樂,也是最悲哀的一刻。快樂在於兩人的美好在到此達到高峰,悲哀在於從此之後失去了排戲的動力。
這也不是誰的錯,畢竟誰在20幾歲會想起愛的多樣性?我們就是在玩嘛、愛嘛、揮霍嘛、燃燒嘛!誰會在高潮那一刻睜大眼睛、反問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得了癌症,他會不會陪我去做化療?如果有一天我掉光了頭髮,他還會不會叫我寶寶?
我也不會這樣問自己,直到我碰到生平第一個女的「朋友」。
我們是在舊金山念書時認識的,不同系,我在中國同學會的活動上看到她,立刻被她吸引。當場打聽,別人說她已有男友。我還是上去攀談,聊完後跌到谷底。是的,她有男友,而且交往了五年!唯一的好消息是:那兔崽子住在西雅圖。
也許是我一開始就知道她有男友,所以沒有非份之想,奇妙的,這讓我和她在一起時更放鬆、更開心。她有另一個在做事的女性朋友,於是我、我的同班男同學、她、她的朋友,我們四個,給了我在苦悶的留學生活中最快樂的時光。星期五下午,我們三人會開一小時的車,到她朋友家,然後在她家做飯吃飯、洗衣洗碗、看《魔鬼終結者第二集》、把一包又一包的垃圾食物塞進嘴裡。我們也玩「國王遊戲」:四張撲克牌,抽到K的人,可以命令另外三人做任何事。在那年紀,「任何事」當然不是吟詩,而是脫褲子。我們也曾玩到,妨害風化,她們的臉上,人面桃花。那種親密,超越大學時的戀愛。但奇妙的是:我們並沒有愛情。人在異鄉,寂寞分秒必爭。我們只是四個孤單的年輕人,渴望在彼此的陪伴下,對寂寞反敗為勝。
不過我的想法太單純。我的同班同學追上了她的朋友。同學在追之前還很有義氣的問我:「你要不要追,你不追我就追了。」我說不要,原因不明,也許我還奢望著有男友的這個女生。四人中有了一對,另外兩人通常會尷尬。我們還好。我竟發揮了人性的光輝,開車送她到機場接從西雅圖來看她的男友。只不過在高速公路上我一直聽收音機,希望聽到墜機的消息。
她男友來時,我都藉口說有考試而躲起來。他男友走了,我又「考完」了。我們又一起去吃飯、洗衣、看電影、找工作。在她面前,我是最糟的自己。我不洗臉、穿拖鞋、飯碗不吃乾淨、腿抖個不停。但她從來沒有挑剔我。她總是說:「Tom就是Tom,他就是這樣才可愛。」說完,她就牽著男友走了。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可愛」不是讚美,「可愛」,是最娓婉的拒絕。
而且「可愛」的有效期限很短。畢業後我去紐約,她留在舊金山。後來我去東京,她去西雅圖。再回美國,我們就失去聯絡。後來聽說她結婚了,卻不是嫁給西雅圖男人。(他X的,早知道我就追她了!)現在我雖然不知道她在哪裡,卻可以感覺到此時她正跟我一起呼吸。這不是愛情,卻比愛情甜蜜。我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個,覺得《魔鬼終結者2》很浪漫的人。
我32歲回到台北,認識了很多女人。有些我喜歡但不喜歡我,有些喜歡我但我沒火花。對這兩種,我都想仿照《魔鬼終結者2》模式,和她們變成「朋友」。在「我喜歡但不喜歡我」這個族群中,沒人想跟我做朋友,也許她們都看過《當哈利碰到莎莉》,知道這只是我「蠶食鯨吞」的陰謀。
在「喜歡我但我沒火花」這個族群,運氣較好。我會主動約她們吃飯,但很少有第二ㄊㄨㄚ。我送她們回家,但她們不會邀我上樓。我到家後會發個簡訊告訴她們,但睡前不會忍不住再跟她們MSN。她們偶爾會打電話跟我聊起追她們的男人,我好像教練一樣鼓勵她們衝鋒陷陣。下一次見面是三個月後,路上巧遇,彼此都說還是老樣子,於是不急著再聚。然後她的手機響了,她一邊接一邊跟我揮手再見,我一邊揮手一邊想起蔡琴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我們成了朋友,或是陌生人。突然有一天,我聽說她要結婚了。起先很生氣,氣她們為什麼不事先告訴我?後來才想通:唉,我跟人家是什麼關係?人家幹嘛事先告訴我?這類「朋友」結婚,我會送禮,甚至去當司儀。但夜裡回來總是失眠,睜大的眼睛裡都是空虛。
如今的女性朋友,因為一開始就沒有曖昧,所以後來也沒有後悔。她們好像家人,看過我狼狽不堪,於是對我的光鮮亮麗,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在她們眼中,我不是才子、不是名人、不是暢銷作家、不是愛情教主,只是跟大多數的單身族一樣,一塊浮木,在人海中漂流;一名賭徒,想贏,但更怕輸。
浮木,可以飄一輩子。賭徒,可以不再下注。我唯一怕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得了癌症,誰會陪我去化療?」媽媽年紀大了,不可能拖累她。哥哥有自己的家要照顧,也只能盡力而為。朋友們各有各的家庭和煩惱,頂多來看我一次。如果我有老婆,老婆可以陪我。但我沒有。唯一剩下的,大概只有這些也單身的女性朋友。
她們給我的當然不可能像家人那麼深、老婆那麼廣,但她們可以給我一種有老婆的男人可能都沒有的東西,那就是「Companionship」。這種陪伴,沒有法律效力或道義責任,於是施與受,就變得比較輕鬆。她們不會睡在醫院陪我,但應該願意為我走私一客麻辣火鍋。她們看到我化療後的光頭,不會傷感或心疼,可能會說:「Tom就是Tom,他就是這樣才可愛。」
陪伴,也許短暫,但自然。也許斷續,但溫暖。如果我得了癌症,應該還是可以找到,一個陪我看《魔鬼終結者2》的人。
◎刊載於2006年7月23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完-
 ...
想跟其他讀者分享心得嗎?請按此連結,進入 ...
想跟其他讀者分享心得嗎?請按此連結,進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