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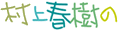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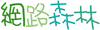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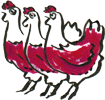
 名家檔案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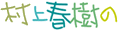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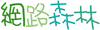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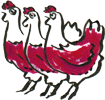 |
|
關於村上的 |
村上春樹的世界 |
|
| 評論 |
川本三郎/作 |
|
|
|
賴明珠/譯 都市的作家
近幾年來,日本新一代的文學作品,往往以「都市」這完全無機的語言當主體,代替「我」或「我們」。
例如「都市的感受性」一詞,所指的並非都市人的感受性,而是都市本身的感受性。不是人類的感受性而是超越人類,將每個人的個性無化之後,僅指都市這個空間的感受性。
現在的都市,與其說是充滿人性味道的生活場所,不如說是一個充滿資訊與記號的無機性而殺風景的平面空間。在這裡人們接觸的是大量的電視畫面,和報章雜誌的訊息,在這裡「生活的真實感」和「人的存在感」日漸稀薄。這樣的都市,與其說是生活的場所,不如說是各種記號與象徵交錯共存的抽象空間來得確切。
這一代的青年,不必到街上去,卻把街上發生的事,帶回房間裡閱讀。對於這些讀者來說,所謂東京這生活空間,已經變成所謂 "Tokyo" 這種失去「生活真實感」的平面空間了。
極大化的資訊圈與極小化的生活圈的乖離,遂成為日常生活的體驗。孩子們的生活,被規範在學校與家之間來回往返。回到家則關進所謂書房的狹小密室裡,大量消費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所生產的資訊。「生活的真實感」越來越稀薄,只有資訊在密室裡紛飛。「中東戰爭」、「波多黎各內戰」的訊息,和電視中「速食麵」、「隨身聽」等廣告同等價值。
都市中的人漸漸失去與他人或事物直接接觸的經驗,卻只從資訊的消費中,得到一些代理體驗式的經驗。
現在都市所擁有的恐怖感,並非從現實中頻繁發生的血淋淋的殺人事件得來的,雖然血腥事件不斷發生,但都市中人所接觸的,並非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卻只不過是乾乾的一則訊息而已。
都市所擁有的這種無機性、記號性,在現在和未來文學上影響如何,實在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在音樂世界裡,近年來顯著的趨勢,可以從Yellow Magic Orchestra(YMO樂團)所代表的「科技熱門音樂」 (Technic POP) 的出現看出來。科技熱門音樂以所謂電腦合成器的機械聲音為基調,並將人類的聲音極端無機化,也就是接近電腦合成器的聲音般的非人性聲音,音樂與演奏者之間,「情感」和「喜怒哀樂」都被否定,音樂越來越趨向於空虛。在爵士樂的領域,也和科技熱門音樂同樣呈現非人性的特質。
在文學方面,對於急遽變化中的都市風景,已呈現追不上的現象。以過去那種有血有肉的小說語言,已經難以描述目前的現況。
村上春樹可以說是現在最受注目的當代年輕作家,是一位濃厚地背負「都市的感受性」的作家。他的作品經常是內容隱藏在風格裡。不,應該說是風格本身就是他的內容。而以往作家賴以支持風格的「生活真實感」或有血有肉的感情,則消失無蹤。
村上春樹似乎只關心都市的表面,而對於都市所提供的「氣氛愉快」的消費生活,則表現出樂在其中的樣子,或者可以說裝作樂在其中的樣子,並以這裝作出來的樣子,做為他獨特的表達語言。
在村上春樹的作品裡,出現大量的商品名稱,包括唱片、作家、音樂家、導演、電影等名稱。他並非想藉以描述什麼新奇的風格,只是覺得都市所提供的商品記號,比「生活」更具親密感。而且嘗試以這些來訴說被記號層層包圍的都市現況。
村上春樹一面選擇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將其記號化,一面在作品中引用出來。他作品的主角,幾乎不用現實生活中的語言,而常引用自己所喜歡的作家的語言,引用喜歡的歌詞。換句話說,他的主角是商品目錄少年、記號少年。因此會話成為主角的獨白,成為一種密室中自閉的表現。例如在《聽風的歌》和《1973年的彈珠玩具》中,大部分的會話,是在所謂「傑氏酒吧」的店裡、床上、汽車上進行的。主角多半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一面談些架空作家、談夢、談電影、談小說。有關「生活的真實性」的話題卻並未出現。主角幾乎不太動,不是躺著就是坐著。這正與生活圈縮小化,資訊圈擴大化的現代都市生活相吻合。在《1973年的彈珠玩具》中,家族、雙親等一概沒出場,並將時間的連續性刻意切斷,僅僅呈現都市表層的現在而已。
村上春樹的世界,經常是「被動的」小世界,在這裡他刻意小心地排除一些會引起混亂的對立場面。正如商品目錄少年,在自己的小密室裡,只與唱片、漫畫、海報和my favorite things為伍一樣,村上春樹在自己的作品世界裡,也只帶進與自己興趣相符合的記號。村上春樹的主角,經常在傑氏酒吧,或酒吧外的木頭欄杆上,或翻譯事務所的書桌前,坐著不動,從這些象徵手法,他們的行動空間變得極端狹小。
村上春樹在接受朝日新聞訪問時,對於自己被稱為「輕鬆派」作家、「都市派」作家,頗不以為然。「其實我也有不喜歡的事,或有血有肉的經驗,曾經騙過人,也被別人騙過……不過我覺得都市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這種享受消費的生活,總不能永久繼續下去,有一天終會崩潰消失……」
從世代論來說,作者的學生時代,即60年代後半,恰逢「越南戰爭」、「大學鬥爭」等「政治季節」,同時也是披頭和鮑比狄倫所代表的藉音樂得到感性解放的世代,因此這種特有的不自由(政治)與自由(音樂)微妙共存所產生外表看似輕鬆的虛無主義,背後其實隱藏著「絕望」。
他們對於「我們只有政治」的上一世代,提出「但是我們也有音樂」的感性解放主張。而對於「我們只有音樂」的下一世代,又忍不住想提出「可是我們也有政治」的主張。這種政治與音樂雙重意識的情緒矛盾,更促使村上春樹走向虛構之途。
村上春樹放棄以往作家以精緻的生活實感所支持的青春小說的表達形式。卻只以敏銳的方法意識、以精選的獨特語言,磨練出一種嶄新的風格,引用大量情報,和嘲弄式的玩笑,裝作出一副「心情愉快」的模樣,企圖以意識的感覺來說故事,而將現代的「不幸」,逆轉為「幸福」。
村上春樹的文學,像一面鏡子一樣,反映出現代社會由平面記號累積成的無機化感性,極端敏銳、新鮮而發人深省。
1980年代的空虛世代
不僅日本稱呼年輕一代的文學為「空虛的世代」。美國自從進入80年代之後,也出現了所謂 "no generation" (指的是什麼也不追求的一代),這些人煙也戒了、酒也戒了、肉也不吃了、裝飾品一概不帶,他們深知自己在都市這巨大的機構中,不過是個渺小的個體,因此並不做過分的感情表現。
村上春樹的主角,肯定自己所喜歡的爵士樂唱片、外國小說、啤酒,這些微小的細節,從這肯定產生了「趣味的房間」,在這裡足夠他「心情愉快」。
《1973年的彈珠玩具》中的「我」,確實是和雙胞胎姊妹共同生活,表面上看來像是自誇很罩得住的青年,其實3個人的關係,幾乎不能算是真正的男女關係,倒更像扮家家酒遊戲似的稀薄關係。對於主角的「我」來說,穿著超級市場開幕贈品T恤的雙胞胎,簡直就像史奴比的布娃娃一樣,他們並不做愛,只是互相擁抱著睡覺而已。
「我們並排躺在涼涼的草地上,繼續聽著芒花被風吹動,發出沙拉沙拉的聲音。」
村上春樹的主角「我」和「老鼠」的關係,令人聯想到史奴比和糊塗塔克的友情關係。史奴比的格言可以說是「我不在乎你們怎麼樣,所以你們也別來煩我。」他不愛跟別人爭論什麼,寧願躺在小狗屋的屋頂上看天或睡覺。如果對村上春樹讚美道:「你的小說充分反映現代青年的心情」或許不如說:「你的小說主角很像史奴比」更令他「心情愉快」吧。
……
|
◆◆
下一頁
|
|
|
 回首頁 |
|
|||||
| ~ 村 上 春 樹 ~ | |||||||
|
繪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