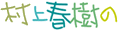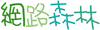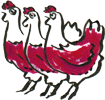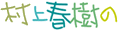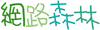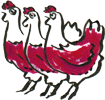|
就算他們說「我們所嘗到痛苦心情你們不可能真正了解」,我想那也是沒有辦法的。真的是說得有理。我想我們是不可能了解的。但總不能因為這樣,話就是在這裡中斷結束掉,從此切斷彼此的對話溝通,因為那樣的話我們哪裡也到不了啊。留下來的只是一種獨斷(dogma)而已。
-- 村上春樹,《地下鐵事件》
我一直是個村上迷。
從很早很早以前鄉村出版社出版、排版像言情小說的《挪威的森林》,一直到近幾年來時報以藍小說系列重新塑造新時代都市風格的眾多小說,村上那種獨特透過語言傳達的難以言喻的情感,總是深深的吸引著我。他的小說作品有一定的慣調,像是以「我」作為主體稱謂來訴說故事、並列世界的虛幻與真實層面等,但是這種風格在《地下鐵事件》出現很大的轉折。
《地下鐵事件》是由村上採訪六十位在 1995 年 3 月 20 日日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中的受害者,將這些受害者的主觀經驗撰寫集結成書,在中譯本近六百頁的長著中,村上首次以真實生活中的「我」出現,相對於以前的小說而言,這個「我」比之前小說中的「我」實在許多,不再老是跟羊男、黑鬼、獨角獸、不知名的黑幫組織等虛幻人物對話或搏鬥,但是也因為如此,讓許多像我一樣的村上迷感覺到有點迷徨、詫異,與之前的文體(註 1)不符合啊!
在初次看完這篇長著之後,我的感覺是相當紛雜混亂的,整理不出個頭緒來;經過幾次細細的重讀,我發現這種混亂似乎是正對著我心目中的採訪寫作觀念而來:我們要怎麼樣用自己的概念來理解別人的概念?就算勉力站在他人的立場來理解事件,我們怎麼樣將「別人的話語」(another's words)放在自己的話語中,集結成報導?文本在重重話語的包圍之下,呈現出的到底是誰的事件、誰的觀點?經由報導所揭露出來的若不是所謂的事實或真實,那麼它是什麼?隱藏在文本之下的,除了傅科所說的權力以外,難道就沒有別的東西了嗎?
當事人的記憶
就算沒有對外人談過,但多多少少也應該會以各自的做法,在自己內心確認事件的記憶,並逐漸客體化。所以人們所說的事件經過幾乎都極真實,往往很視覺性(情景性)。
但那再怎麼說終究還是記憶。
……正如一位精神科醫生說過的那樣,可以定義為「所謂人類的記憶,只不過是人們對發生的一件事所做的<個人解釋>而已」。例如透過記憶這個裝置,我們有時會將一個體驗改編成容易了解的樣子。將不方便的地方省略捨棄。前後顛倒。不清楚的地方加以補充。自己的記憶和別人的記憶混合,必要時則交換。我們會極自然地,潛意識之中不知不覺地在這樣做。
說得極端一點,或許「我們的體驗記憶多多少少已經故事化了」。(pp. 568-569)
村上所說的「記憶裝置」,其實就是人與自己對話的語言形式。我覺得討論採訪寫作的語言機制,第一個要處理的中心點應是當事人對於自己經驗的知覺。在 Norman Fairclough(註 2)的分析架構下,位於傳播事件論述的中心點是文本;然而,更進一步的,我認為報導文本的核心在於當事人的記憶。雖然報導中不免必須經由報導者的轉述、重寫、刪節、組織與合併,但這些必然環繞在當事人記憶之外的轉變;核心點必定在當事人的記憶,雖然它不見得實質存在。
記憶,是經由語言加以定泊。當我們對某個事件產生模模糊糊的感覺時,不經由語言,它永遠存處於模模糊糊的狀態;透過語言的詮釋與命名,事物的概念才得以落實。語言就像是一面鏡子,不透過鏡子,人們永遠只能片段地看到自己的手掌、膝蓋、腳趾或肚皮;唯有透過鏡子,破碎的片段才得以組合成完整的整體。拉岡將語言這面鏡子比喻成哈哈鏡、柏拉圖的洞穴;而傅科則是認為人們經由語言來進行自我告解的懺悔,重新將自己編織進符合道德規範的正常人。無論如何,經由語言定泊的事物,早已不再是原始經驗的模糊狀態;如果說原始經驗的模糊狀態才是真正的事物本質,那麼語言已經使我們離開這個本質,愈加以闡述、愈加說明,就離本質愈遠;這也就是現象學派人士追求的「還原」(reduction),還原到未說明之前的本質。
然而,追求去除語言的事件本質既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如果所有的經驗都需透過語言來加以定泊,不如就正視這種必然的結果,因為意義的產生必然落在文脈當中。當然,我採取這種面對被採訪者的角度,已經是明白放棄 Sausser 所追求的符號具與符號義之間明白、清楚的對等關係,符號具背後是不是對等著一個確實存在、永恆不變的概念已經不在重要,將記憶本身視為真實的部份,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部份。村上顯然在這點上,也持同樣的看法:
我在採訪時,經常保持這樣的基本態度,那就是「他們所說的化,在各自述說的文脈中,都是明明白白的真實」,現在也還明確地保持著。這結果,從同一個現場同時體驗過的不同人的話,可以看出細節有些出入,但我還是照著略有矛盾的情況原樣提示在這裡。我想可能出入和矛盾本身應該就會說什麼吧。在我們這樣多面性的世界裡,有時候不整合還比整合更雄辯。(p.569)
是的,有時候不整合比整合更雄辯。 Raymond Williams 在進行《關鍵字》的討論時,不是也特別指出,當字詞出現差異之時,正是探索意義變化的絕佳時機?(註 3)
撰述者的轉述
順著 Fairclough 所提出的研究架構,第二步驟是走向論述實踐的層次,關注的焦點文本的產製與消費,我認為這是目前消費市場伴隨大眾媒介盛行的時代中,最為錯綜複雜、盤根錯節的部份。我想將重點放在報導者一方,也就是文本產製過程中牽涉到的語言過程,包括報導者如何面對「當事人的記憶」以及他本身的態度與世界觀;關於文本的消費部份,牽涉到廣泛的閱聽人研究,村上無意處理,當然也是我沒有辦法與他對話的地方;他所要檢討的是作為一個報導者的態度、做法以及報導的意義,而這也正是我想要與他對話的重點。
前面已經提到,當事人的記憶已經在自我對話的過程中,讓原初的感覺與經歷起了變化;接下來,對於報導人而言,他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記錄當事人的記憶,在一場關於參與觀察法的論戰中, Laurel Richardson(註 4)曾經指出,沒有任何一個研究可以完全記錄真實,研究者或多或少擷取他認為值得記錄的事實,但是這種擷取出來的結果,卻被用來代表研究對象的整體。而村上以更實戰經驗的方式,來提出語言轉換的問題。
錄音帶就那樣交給專家,所謂請人將「錄音帶原稿化」。也就是除了明顯屬於採訪目的所不必要的部份之外,其餘發言都原樣保留地變成文字處理機上的活字。當然,有時文字變成相當長。還有正如我們大部分日常會話那樣,話題往往跳東跳西,或走進叉路迷失或中途消失了,之後有突然復活起來。於是必須將那內容選擇取捨,前後對調,消除重複的部份,將文章分節或串連,整理成某種程度容易理解的文章,編寫成適當長度的原稿。因為光讀「錄音帶原稿化」往往還無法掌握細緻的感覺,因此常常要重聽錄音帶,做細部的確認。(p.13)
雖然村上想要交代的是-他們是非常謹慎地在處理物質層面的問題,但是這也更進一步地牽涉到報導者如何處理、記錄他所報導的事物。
我更關心的是,語言在這個記錄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Gunther Kress 和Robert Hodge 曾經就語言的心理轉換層面提出,我們看到的物體是包含著物體本身及其狀態的整體,這是視覺層面的知覺,但是在語言呈現上,卻必須將這個整體劃分為主體與動作,如說:「魚兒在游泳。」魚兒是主詞,而游泳是動詞,但是實際的知覺層面這二者是合為一體的。 Kress 和 Hodge 稱呼這種視覺/生理到語言/心理的轉換過程為知覺鏈(perceptual chain)。同樣的,當我們進入一個場域進行觀察報導時,所感受到的整體必須化為語言來表達;當我們看到某人、聽到某人、感受到某人氛圍的整體,須經由知覺鏈切割為語言組合。因此,報導者所報導出來的東西,也不會再與他所觀察的事物整體相符,語言使它們之間存在著轉換的過程。
村上提到的是聲音記錄(錄音帶)與文字記錄之間轉換的問題;而我更想說的是,任何一種文本內容所闡釋出來的意義都與文本本身的形式緊緊相繫,即使就同一個主題而言,文本形式的轉換也必定伴隨著意義的變遷。就像是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小說原著,勢必與關錦鵬導的《紅玫瑰與白玫瑰》電影不同,也與林奕華編寫的劇本不同,雖然他/她們處理的是同一個主體、同一個故事架構。張愛玲鮮明華麗的文字,讓身為讀者的我憑著自己的生活經驗,將故事在腦海中轉換成一幕幕的畫面;這與關錦鵬導出來的電影文本,伴隨著音樂、影像與演員造型所呈現出來的整體感,是完全不同的。同樣的,帶著耳機聽到的錄音帶內容,與親身經歷的訪談過程不同,與轉換為文字的記錄不同,口語說話與文字本身就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即使硬要從中間歸納、凸顯某些共同點,也勢必會忽略、隱藏其相異的特點。
採訪時身歷其境的感受,幻化為文字,勢必無法重建事件的整體樣貌,錄音帶只是重新喚起採訪者記憶中的感受;如果這是必然的結果,那就不必過於煩惱,我覺得 Richardson 從一個解構主義立場提出一條新的解決之道,他認為無論什麼樣的真實記錄,都包含著研究者/採訪者的選擇、擷取與建構,身為研究者/採訪者應當注意、反省與察覺自己在研究過程中關注的問題焦點、記錄那些對話,進而在文本中找尋失落的地方以及被邊緣化的事物。
這種反思的態度,與專斷性的決定、摘取、節錄被採訪者的話語是不同的;很不幸的是,後者卻是現今普遍存在大眾傳播媒體之中,因為種種時間、版面、畫面的限制,記者任意的選取,最終的結果卻是造成被採訪者對於新聞媒體的不信任。村上描述的雖然是存在日本的媒體現象,在台灣卻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多半的情況又因「已經不想再回想那個事件」「不想再跟奧姆扯上關係」「無法信任媒體」等種種原因拒絕採訪。尤其對媒體採訪的反感和不信任遠比預料中強烈,因此光說出出版社的名字電話就被卡鏘地掛斷,已經是家常便飯的事。(P.15)
以我們來說,對於很快就答應證言請求的被採訪者,我們盡量避免造成現實上的麻煩,並極力避免讓對方感覺不快。為了抹去對媒體所感覺到的一般性的不信任感,我們但願不要讓對方有「好不容易信任你協助你,這信賴卻被出賣」的感覺。(P.17)
〔和田嘉子的訪談記錄,一位受害人懷有身孕的妻子,事後產下遺腹子〕有一次因為某種原因,我上過電視。播出以後電視台的人告訴我說「反應很熱烈呦」「來了好多信」,但卻什麼也沒寄給我。我想他們真隨便(笑)。我已經不想再上電視了。絕對不上了。他們並沒有傳達真實的事。我希望他們能傳達真實,但電視台只播放對自己方便的地方而已。我真正想講的部份他們卻不播出來。(p.551)
轉喻後的被報導人
就更細微的語言層次來看,我們在指稱某人時,難免會運用語言機制的轉喻(metonymy)功能,即是部份代表整體。隨便一翻開報紙的社會新聞版(註 5),處處可見的對於犯罪人、受害人的轉喻指稱:「因盛傳有『幼齒』陪酒,艷名遠播,不僅吸引酒客趨之若騖……」,用年輕貌美來指稱未成年陪酒少女;再如「從菲律賓進口石材夾帶槍械走私案,逮捕林全德、林俊昌、廬次郎等嫌,起或四把烏茲衝鋒槍....」,用攜帶槍械的特質來指稱槍火嫌犯。問題是,用年輕貌美來指稱未成年少女,難道她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特徵,沒有朋友、沒有生活、沒有歡喜、沒有矛盾與為難;帶有烏茲衝鋒槍的嫌犯,就沒有父母、沒有妻兒、沒有內心衝突?當人們被簡單化約為某種類型的人,將某些刻板印象運用轉喻來指稱整體時,其實已經造成閱聽眾與「發生這些事件的人」之間的距離,呈現是「那是發生在那個世界的人,遠遠的與我們不相關」的心態。
像這樣採訪撥出許多時間和部份在被採訪者的個人背景上,是想讓每一位「被害者」的容貌細部都儘可能更明確真實地浮現出來。因為我不想讓每個活生生在那裡的肉身的人,只成為「沒有臉的許多被害者中的一個(one of them)」而敷衍了事。或許因為身為職業作家也有關係,我對「總和性的、概念性的」資訊這東西不太感興趣。而只對每一個人具體的-不可能(難以)交換的-存在方式感到興趣。.....因為照理說那天早晨,搭地下鐵的每一位乘客,應該都各有臉、有生活、有人生、有家人、有歡喜、有煩惱、有戲劇、有矛盾和左右為難,也應該有結合這些形式的故事才對。換句話說因為那也就是你,而且也就是我。(pp.18-19)
在芸芸眾生中,如果新聞報導的選擇焦點仍是關注在衝突性、特殊性、重大性的事件之上,我想運用轉喻的方式來標示事件中的人物是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選擇?如果色情行業從事人必須以「妖嬈美豔」來指稱,強盜殺人犯勢必是「抹滅人性的禽獸」,這種由部份特徵來指稱整體樣貌的做法,將會使人們將這些犯罪人也好、受害人也好,都歸類在世界「異常」的一方,他們/她們與「正常」的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沒有辦法從報導中想像殺人犯也有父母妻兒、也有愛好憎惡、也有他/她的成長背景與遭遇,也有善良溫和的一面,因此當鄰人變成殺人犯時,往往給我們帶來相當大的錯愕,因為報導所養成的慣性思考中的殺人犯形象與鄰人形象是不能吻合的,殺人犯幾乎是不具有「人性的」。如果我們的論述一直存在於這種二元對立、善惡分明的分類系統下,「異常的他者」與「正常的我族」旗幟將會永遠鮮明,二者間的鴻溝也將永遠存在。
抗拒二元對立的可能
只要去除多餘的裝飾品的話,大眾媒體所依存成立的原理結構,可以說相當簡單。對他們來說,所謂地下鐵沙林事件,簡單說就是正義和邪惡、正常與瘋狂、健康與畸形的明白對立。……然而在這巨大共識之流的盡頭,事件發生以來以經過兩年歲月,身處「正常」的「這邊」的我們,在巨大共乘馬車搖晃前進下,到底到達什麼地方了﹖我們從那衝擊性是建中到底學到了什麼?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了﹖……換句話說,「奧姆真理教」和「地下鐵沙林事件」給予我們社會的重大衝擊,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被有效地分析出來,那意義和教訓也尚未被整理成形。這本書寫成的今天,我依然不得不抱著這樣的疑問。事件是否正繼續以「總之,這大概是瘋狂的集團所引起的,例外而無異議的犯罪吧」的形式被解決掉呢?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把真理教這個「事物」純粹當作是別人的事,當作難以理解的畸形東西,從對岸用望遠鏡眺望的話,我們可能無法到達任何地方。(pp.556-557)
李維史陀從親屬結構、儀式行為與神話傳說,歸納找出人類思惟深層結構中的二元對立模式,我想他是沒有錯的;人類的原初感知、經驗與情感,在經由漫漫語言之路的形塑之後,的確傾向於黑白分明的簡單二元對立。就像是傅科所說的,論述形構把「瘋狂的異端」集中進行監控與管理,以確保「正常的我方」安全而自在的生存。問題在於我怎麼樣可以確定自己是站在正常的一方呢?我也常常在私底下進行一些不被人知、躲躲藏藏的「惡事」,甚至我也不敢確保我在眾人面前說的話、做的決定就是屬於「正確的一方」,那一天當歷史洪流轉變之後,我是不是也會被放在「異常的一方」呢?如果語言與論述的結構,勢必逼著我們將思考、感知趨向於二元對立,那麼在這個語言的桎梧下,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
層層障礙下的語言溝通
揭露這些語言運作的機制,是不是就代表我們應該放棄語言,從此縫上嘴巴、貼起膠帶,讓混沌的世界就存在於混沌的狀態之下?這種想法,又是長久以來習以為常的語言論述形構,讓我陷入了二元對立的絕對當中。世界不是黑白二色,事物也非只是善惡區分;語言既不是白得像透明的鏡子一般,也不見得黑得像萬惡淵藪一樣。如果人們的思想進行與相互溝通勢必需要經由語言論述形構進行,那麼是不是有可能發生超越二元對立的論述規則呢?
確實從由於地下鐵沙林事件而深受傷害的被害者這邊的心情來說的話,寫這本書的我是從「安全地帶」來的人,是隨時可以回去那邊的人。就算他們說「我們所嘗到痛苦心情你們不可能真正了解」,我想那也是沒有辦法的。真的是說得有理。我想我們是不可能了解的。但總不能因為這樣,話就是在這裡中斷結束掉,從此切斷彼此的對話溝通,因為那樣的話我們哪裡也到不了啊。留下來的只是一種獨斷(dogma)而已。(pp.573-574)
是的,我想是有可能的。揭露是改變的開始,同樣的,提出這些採訪報導語言運作的機制,也是進一步思考轉變的起點,再套句村上的話:
有了這種認知(彼此互相都有這種認知),但仍然嘗試去超越克服時,撇開論性的追究,我想或許可以找到更深厚的解決之道吧。(pp.574)
註釋:
- 如果將文體視為是劃分文本範疇的方式,我覺得村上的小說可以說是已經自成一體,擁有他自己特殊的結構、說話的方式以及關心的重點,他都是以第一人稱向讀者訴說著故事,故事中大都存在著一些虛構的人物(我覺得這些虛構人物只是用來凸顯、指涉現實世界中的某些人性特徵)與虛幻的世界,有趣的是他的每篇小說之間也許沒有明顯的關連,但是故事線卻隱隱約約地相互呼應。關於村上小說的文體特徵與意涵,我想至少要另一篇文章來另外處理,但是他的文體確實是讓想我這種村上迷,對於他的小說產生某些企盼。
- 這邊所說 Faiclough 的分析架構,是出自於1995年他所撰寫的《Media Discourse》,他認為對於傳播事件的分析可以分為三層,第一層是文本,偏向語言學;第二層是論述實踐,也就是關於文本的產製與消費;第三層是社會文化實踐。
- 這種說法,其實跟 Williams 原本的說法有些差異。 Williams 在討論字詞的轉變時,觀察到一般人經常批評報紙對於某些字彙的使用是錯誤的、與該字彙原初的意涵不同, Williams 認為這種字詞的錯誤或衍生使用,正是代表著當代某些社會或文化的轉折,是值得特別關注與研究的焦點。
- Laurel Richardson 在1995年時,與 William Foote Whyte 等人針對田野調查法的方法論問題進行論辯,主要爭論的焦點在於研究者是不是能夠代表被研究者說話,研究者的觀察記錄可不可能等同於真實世界等。文章出處是 Richardson, Laurel. (1996). 'Responses to Whyte; ethnographic trouble.' Qualitative Inquiry, 2:2, 227-229.
- 我真的是隨手翻開 1999 年 6 月 12 日《中國時報》的 8 版社會新聞,下面的例子均出自此處。
原載《當代》雜誌第 150 期
Post Time: 2000/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