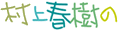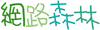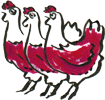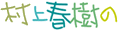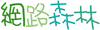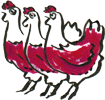|
涼爽的夏日雷雨午後,空氣中飄著一股溼潤的雨味。在這種慵懶的下午,最適合煮杯咖啡歐蕾,悠哉悠哉地念念小說、發發呆、做做白日夢。在念了研究所以後,我發現我已經喪失用酒精咖啡壺、讀秒煮咖啡的閒情逸致,拿起美式咖啡壺,磨豆子、插電、放水、開關一按,就去溫牛奶,順便溫溫我的馬克杯。將身體埋進柔軟的單人沙發裡面,我拿起前二天剛買的村上寫的《開往中國的慢船》,隨手就翻到了這麼一段:
「上次我在動物園看見貓喔。」他一面打開啤酒瓶蓋一面說。
「貓?」
「嗯,大約兩星期前,我到北海道出差,那時候我走進附近的動物園去看看,結果有一個小柵欄掛著『貓』的牌子,裡面躺著貓喔。」
「什麼樣的貓?」
「非常普通的貓啊。茶色條紋,尾巴短短的,胖得不得了。牠就那麼大辣辣地橫躺著呢。」
「一定是貓在北海道很稀奇吧。」我說。
「怎麼可能。」他說。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貓就一定不可以進動物園呢?」我試著問道。「貓不是也是動物嗎?」
這是習慣哪。也就是說貓和狗都是到處可見的動物啊。沒有必要特地花錢去看。」他說。「就跟人一樣嘛。」
「原來如此。」我說。
--村上春樹(1998)
為什麼貓就不能進動物園呢?
腦海中浮出的貓的形象,不是懶洋洋地躺在屋頂上晒太陽的貓,就是躲在路邊停車車下、一旦有人接近就一溜煙地跑掉的貓,就是沒有像老虎一樣露出無辜表情、關在柵欄裡的貓。
那麼,動物園裡都住著什麼樣的動物呢?
有帶著金色鬃毛、神態威猛的獅子,有肚子像牆壁一樣壯碩、用鼻子捲著牧草吃的大象,還有半臥在水中、老是張大著嘴打呵欠的河馬……,但是無論是哪一個,牠們身處的柵欄前必定擺著一個牌子,上面著名著「獅子」、「大象」或「河馬」,旁邊還附註著英文 " lion " , " elephant " 與 " hippo " ,並且寫著牠們的科屬種以及生活習性等。
我覺得動物園是最佳上符號學的地方。試想想,當我們走到一個廣闊、透天的柵欄前,眼睛正看著一種脖子長長的、長到高過小樹頂端,正低著頭吃著樹頂上葉子的一種具有漂亮黃棕色格子毛的動物,心裡逐漸對於這種動物形成「牠」的印象時,身前的告示牌便直接定泊了我們對於這個生物的概念,告訴我們牠的名字是「長頸鹿」。然而,這個具有命名功能的告示牌,是由社會共同賦予的力量,不信你試試看指著一群標示著「斑馬」的動物,大叫「好多台灣獼猴啊!」,你將會發現身旁的情侶會用懷疑的眼神瞄你,而周圍的家長恐怕就會趕緊拉著小朋友的手紛紛走避。
但是,反過來說,有固定的名字,就會有固定的概念嗎?雖然我不會離譜到把老鷹看成雉雞,也不會把斑馬當成台灣黑熊,但是在我心目中的馬跟你心目中的馬會是一樣的馬嗎?我心目中的馬除了動物園裡遠遠遙望的馬的形象,還包括有我新婚蜜月時騎在馬背上的柔軟記憶,你的馬跟我的馬有一樣的感覺嗎?
我又想到大學四年級的那年暑假,在得知考上研究所後,無所事事地找了個安親班跟小朋友玩,順便賺點零用錢。記得在一個遊戲裡,我讓小朋友輪流到台前來表演他們曾經看到的動物,讓其他小朋友猜。我們猜過了豬、狗、老虎、大象之後,有一個小小班的小朋友,也就是剛從幼稚園畢業、準備上小學的孩子,走到台前來,他蹲在地上、雙手環繞著緊緊合併在一起的雙腳、把頭埋在膝蓋裡。然後我們就開始猜了:
「小白兔?」
他搖搖頭。
「小老鼠?」
他又搖搖頭。
台下的小朋友已經開始亂叫起來:「鱷魚」、「蟑螂」、「土撥鼠」、「綿羊」……,後來連「石頭」、「芭樂」都出來時,我看那個小男孩的眼框已經有點泛紅,趕緊叫他起來,對他說:
「你表演得很好啊。大家鼓勵鼓勵……。那你要不要告訴我們答案是什麼呢?」
他嚅嚅囁囁地小聲說出:「是雞」。
這就有點難倒老師了,我說:「雞?為什麼呢?」
他很委屈地解釋道:「我看我媽媽從超級市場買回來的雞都是這個樣子的啊?!」
語言學家的索老大(Sausser)說的符號具與與符號義的連接,在這裡就出了一點問題,誰說在符號系統中的符號具一定對等著相同的符號義?人家那個小小班的小朋友所說的那隻「雞」跟大家的不一樣,也不代表「牠」就不是一隻雞?法國那個寫《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的小說家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所畫的「恐怖」的「蛇吞掉大象」的圖畫,還不是被誤認是一頂帽子?
想到那群有創意的小朋友,我就忍不住從心裡笑了起來。一口把剩下的咖啡喝掉,我又開始陷入自己創造出來的白日夢中,原本那個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答:「為什麼貓不能擺在動物園裡面?」
那麼,人可不可以擺在動物園裡?假如原因像村上說的,擺來展示的東西是因為牠的稀有性,那麼,人大概就進不了動物園裡,因為在街上看到的到處都是人啊?不過,這也不一定,台北街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珠的人,如果來了一個藍皮膚、金頭髮、紅眼睛的人,可能就會被擺到展示區。台中不是有個九族文化村嗎?那裡的展示不就是以人為主要展示品,那裡有人唱歌跳舞、舂米磨麥,還可以陪你拍拍照、留個影。
到底,這個展示者與被展示者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差別呢?人類與動物的差別在哪裡?平地人與平埔族人的差別在哪裡?這種展示到底透露出什麼樣的意涵?
的確,這樣的展示可以事物的關係變得透明化,符號具與符號義的連接關係清楚明確,這個系統可以告訴我們這個是「標準」的馬,那個是「正常」的牛,小小班的那位小朋友表現出來的雞,就是與我們平常認定的「標準正常」的雞不同,所以被認定是「異常」,沒有人能夠理解。
然而,展示不只是展示出「標準化」的符號指涉對象;進一步的,是讓被展示的一方被清楚展現,而有權力的一方卻隱藏起來。動物相對於人,因為人的權力大,所以動物只好被展示;平埔族相對於平地人,因為人少力薄,所以只好被展示;那一天如果真的像電影演的一樣,外星人攻佔了地球,人類大概也會被所進柵欄裡,外面標示著「男」、「女」、「蒙古種」、「亞利安種」、老中少,黃白紅黑……。
研究權力與論述的專家傅科,把這種展示系統推到極致,便成為你我彼此、自己對自己的互相監視系統。每次我在看到傅科闡述邊沁的圓形監獄時,就想到我慘淡的高中生活。在我那個以升學率為最高指標的私立學校裡,充分發揮了監視的力量。一般上課,都是由一個老師站在高高的台上,俯視著台下烏鴉鴉一片學生;在我們偉大的校長領導下,我們的教室裡面同時存在著二個老師,前面是口沫橫飛的授課老師,後面則坐了一個我永遠不知道她到底在不在、在幹嘛的級任導師,中間則擠著我們五十個頂著西瓜皮、推著厚厚眼鏡的學生。級任導師監視學生,順便也監視授課老師;授課老師為吸引學生準備的笑話,還得留意是不是限制級的。我永遠記得,不曉得在哪一堂課打了個瞌睡,被級任導師從後面猛打一個腦袋瓜子時的心驚。
前一段時間國民 IC 卡吵得正熱的時候,我又回到高中時被打頭的夢魘裡,我有點擔心那一天我突然想要跟老公去某個旅觀幽會一下,會在國家發給的年度活動記錄登錄下來;或者哪一天不小心在百貨公司奢侈浪費一下,國稅局年終的時候會「好心」通知我先生,這一筆款項可扣稅喔!我實在有點擔心,在這個行動愈來愈透明化的社會裡,我可能會被放在單面鏡的柵欄裡,哪一天還可能還會有隻不知名的手,打得我暈頭轉向都不知身在何處。
我很慶幸貓不必住在動物園裡。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要當隻貓。
原載《當代》雜誌第 149 期
Post Time: 2000/0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