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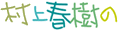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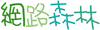

 名家檔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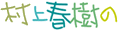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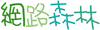  |
|
|
對話空間 29 |
|
|
|
主題:關於疏離 ◆蒼涼與疏離 ( 李友中,99/08/08 )
在看到許多模仿村上文字的作品後,我們可以感覺到由於華人社會缺乏某種東西,使得村上春樹文字很容易流於自我陷溺的通俗愛情故事和美食文化主義象徵。這兩種結果都是由於缺乏某種意識,就是疏離感。 疏離感,是一種格格不入的狀態。那是講究實用的台灣人很難了解的狀態。在台灣,每個人都在說話,無論對現實滿意或不滿意,總是有所表達。而疏離感卻是完全無法表達的狀態。疏離者並非不會說話,而是無法說話,一種失語的狀態。我可以想到的一個稀少的例子是幾年前自殺的三毛。三毛寫了很多本書,是各種勵志演講會的熱門講者,告訴人要樂觀進取,本身更是積極熱誠友愛的象徵。然而最後她卻選擇一人孤獨地走向沒有光線的所在。她突然離去的行為不被理解,很少人從疏離的角度看待。 疏離感是一種奇怪的行為。疏離者處在貧弱的現實裡,通常以華麗的虛偽過活。因此,村上斷片式的文字、記號取向、美食與抽象主義、輕快的幽默感、其實不過是一種華麗的虛偽。很可惜,台灣模仿村上文字的人卻經常沾沾自喜於陷溺這種村上感覺。而對於貧弱的現實,或稱為不毛的疏離感,卻渾然不覺。 比較起來,日本人雖然有牢固的團體傾向,卻因此有產生完全疏離的可能性。我在日本時,也經常感到身旁有懷疑世界真實性的人。反而華人社會的結構雖較鬆散,卻像蒼蠅紙一樣,把每個人都網住,無論滿意或不滿意,就是沒有人懷疑。像三毛或張愛玲那種疏離、孤絕、然後消失,再也無法尋獲的人,在台灣是稀少而不可解,在日本是較普遍而可以被理解。在台灣,從來沒有出現過serial killer,連續殺人者是一種完全反社會人格,是拒絕與社會對話的。那像陳進興嘰里呱啦講一大堆話。當然,這也沒有所謂好或不好。 我覺得村上作品受到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讓書中的主角扮演守候者。站在真實的邊緣,默默等待代表救贖的來電,雖然那是永遠等不到的電話鈴聲,卻讓讀者感到一絲溫暖。 村上春樹的都市記號學般的文字,其實是一種溫暖的反叛,為了避免凝視疏離者空虛的瞳孔裡「有如地底的冰河般,堅硬冰凍的暗黑空間」的一種華麗的虛偽行為。想不到,台灣的村上文字模仿者卻當了真,把澀苦的感傷當成浪漫想像。終極原因是,現實取用的社會比較缺乏疏離者的緣故。 李友中你好,我是JuliaHsu 我想我非常可以認同你的看法。 只是,不只單純是疏離感可以造成這麼大的迴響,也許也牽扯到新價值觀的問題。或許,村上的讀者們的確在作品中第一次獲得了所謂疏離感的相同感受之認同。可是雖然不十分了解你的疏離感的定義,但我想從村上作品中所得到的,是一種個人可以被認同與接受的價值觀。那不只是與社會有沒有積極參予的過程,而是所謂的單獨個體也可以在社會中存在的意思。不管這個個體是否在週遭有團體的約束力。 當然這或許和你所說的疏離感是同一回事,不過,現代社會中有一種傾向是不能去忽視的,那就是自我的強烈抬頭。或許在我們經歷過日本和台灣的生活環境之後,我們會認為台灣的人們就像你所說的,大眾雖然沒有團體的約束卻像是被一張蒼蠅紙黏住一般不能動彈,可是,對於新世代的人們來說,來自群體的束縛可能比我們想像的少的多,與其說是群體那不知名的束縛力,不如說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之後的社會,各式各樣的資訊與價值觀充斥,讓人置身於其中不知如何 安置自己的價值觀與人生觀。所以村上在此時的進入,正好讓讀者們了解傳統的價值觀是可以擺脫的,去認同自己並非是罪事。尤其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台灣的教育體制並不鼓勵表現自我,我們被教導成要謙虛,不可過度的強調自我的想法。被綁在這樣的基本觀念下,說真的,當你想表現自己時,卻有很多時候會不知所措。(或許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台灣這幾年流行的一窩蜂現象,不論是股市,政治……,畢竟附合他人簡單多了) 所以,雖然說台灣的讀者們好像在追尋一種華麗的,浪漫的,卻不知本質為何的村上文學,但是換句話說,或許可以解讀成台灣的讀者們(或是新人作家們)找尋到了一種新的表現手法,而那種手法正好可以適度的表達出他們遲疑已久的心情。 不過,我個人的想法是,像這樣的借用也可能只會是一種過度期的風潮,當台灣的讀者們或新進作家們在一陣子這樣的模仿中,獲得了自我更適切的表達手法後,受限於村上外來作家的身分,他終將被淡忘,畢竟文學領域中還是本土文學的力量比較強大,不是嗎?另外說句沒什麼意義的話,不要拿陳進興與serial killer相比,這樣說也許很奇怪,但他甚至沒有當serial killer的智慧,相信你可以同意! 人類的社會都有著一種共通性,只是因為地區性和民族風的不同,而使著呈現出來的熱鬧和孤寂有著奇怪的對比,如果說華人的社會是一團鬧哄哄的蒼蠅紙,但是黏附在其上、製造出哄哄然聲響的「華人」就是不疏離的嗎? 同樣的疏離在法國、美國和台灣,或者中國和日本,都有著其自然而然形成的獨特音律,那一種與生俱來,或深或淺的孤寂,因著那孤寂而使得人們疏離了,這是誰也逃避不了的,如果你在每個國家的街角少少地站上一會,屏息地──只要一會,你會在每個地方都發現同樣的東西。 就像音樂聲響一樣,搖滾樂的孤獨和抒情音樂的孤獨,鬧哄哄的孤獨和安靜的幾乎沉入戈壁沙漠的孤獨,每到一處那孤獨也就只是換上另一件不同的衣裳而已。 有時我在想,我們用著各種豐湃的知識和社交禮儀掩飾著裸露的那些疏離,出了社會越久,就被教導的越理所當然的必須明白,這樣的掩飾,實際上是禮貌的一種。 從少年開始,我就覺得世界是透明的,如果以X光的原理來說,基本上人也是透明的,但是萬事萬物都有我們自己加上去的濾鏡、或者物體本身所製造出來的保護效果、或者其他之類的雜質,於是便很難看的清了。 我們只選自己想看的看,不想看的那些怵目驚心通常就想盡辦法漠視,而所謂的「怵目驚心」倒也不是可怕或者什麼之類的,而是「看清」一件事物的本質。 這方面我不大會解釋,因為並不是發生了什麼,然後你會對那件東西感到灰心,而是有些事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令人痛苦的。 我到了很後來很後來的時候才學會了怎麼樣不去看見一些,也不算是學習吧?只是好像時候到了,就有一扇門關了,另一扇門開啟,或者兩扇門都開著,然後被風暴困的團團轉,或者兩扇門都關了,變成一種真空狀態。 但是說實在的,我到現在還是不大適應太接近別人,如果一靠近就必須承載別人的痛苦悲傷或者林林總總的情緒之類的(即使不用交談),那真的很辛苦。 話說著說著就離題了,有沒有人發現自己其實不是自己,世界上有十數個自己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身分和面目在不同的空間中存活著,而在意識些微的某處,我們會像行動電話一樣收到那邊的影像聲音之類的,單向的──。 你看的見他、聽的見他、但是他看不見你,聽不見你;反之亦然。 而這是不是所謂的疏離感呢? 而那隻白色的、有著漆黑雙眼的不說話的貓咪,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為何有人會排隊去麥當勞搶購,或許真的是跟風吧?等鋒頭過了,她便又如同光芒逐漸黯淡的明星一般逐漸地讓人覺得不甚稀奇了。 但是想找個東西依賴沉迷的天性,卻也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有人永恆的活在追逐之中,有人隨著時節變化不停地搜尋著新獵物、有人遇見了某事某物,便心甘情願地讓依賴變成一種責任,這之中的曲折趣味,或許是要各人去體會的了。 就像疏離感在每個不同國度裡有著自己的表現手法一樣。 李友中先生:您好,我是Alan Huang. 完全贊同您的推論過程,但個人對推論結果卻無法理解。「終極原因是,現實取用的社會比較缺乏疏離者的緣故。」是這樣嗎? 我想了一想,如果說台灣比較缺乏疏離者,也許不能稱為沒有道理吧。或許更恰當的說法是,台灣社會的疏離感,和日本或北美社會的疏離感有所不同吧。 您舉了十分清楚的例子。我沒讀過三毛的作品,您說她「告訴人要樂觀進取,本身更是積極熱誠友愛的象徵」,但最後卻選擇了自殺,這不是疏離感是什麼?百分之百同意。我不是批評三毛(沒看過無法批評),但這段描述我覺得十分貼近台灣社會。台灣不是到處都在流行勵志書籍嗎?書店舉目望去,都是要人變得樂觀開朗、積極向上的封面,連坊間的一些不管是升學補習班、減肥班或者「潛力開發課程」,也都是打著「三個月成功」(諸如此類)的招牌。 這些訊息背後的「後設溝通」,就是「失敗即罪惡,所以你不可以失敗」。 這種「現實取用的社會」中的一窩蜂現象,我認為,表面上避免了疏離感,但其實卻將疏離感「潛抑」(repress, 不知不覺的壓抑)到更深的地方。在個人,也許最後以自殺作為了結;在社會,卻可能以更怪異、對社會危害更大的方式來呈現。日本有文藝傳統,但台灣有嗎?村上春樹自稱年輕時不喜歡川端康成,姑且不論他不喜歡的原因,但至少他還有川端、三島、芥川、谷崎等人(可以讓他不喜歡)啊!在我們的社會中,純粹的文字創作向來被壓制:要不就是被文字獄般的檢查系統,要不就是被社會的普遍功利傾向所壓制。如果一個社會中,文字並不是一種情感的合法出口,那麼疏離感(如果有的話)要往哪裡去呢? 另一點,我認為台灣社會和日本社會最大的不同,不在於社會結構的鬆散或緊密(基本上我認為兩者對個人的箝制都頗嚴酷),而是因為台灣社會有著共同的敵人(就是中國--不用再說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吧!)。愛默生不是說「戰爭使人更靠近生命」嗎?在有敵人,有危機意識,生存基本條件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不容易出現疏離感。 疏離感,是一種「單人的領域」、「孤獨的領域」;那和雙人或多人領域中的對話是截然不同的。在單人領域中無從對話,也不需要對話(不能作「有對象」的對話)。在壞的方面,它阻斷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構成了各種精神病理的根源;在好的方面,它卻擁有強大的創作可能。個人最佩服村上春樹的地方,在於他把「疏離」這種「失語」的狀態,用各種形式的「語言」(很多是他所創造出來的)講的這麼清楚,「人人心中所有,筆下所無」,好像為這個時代發言似的。而台灣社會或許仍有強大的團體約束力吧,對村上的反應仍然兩極化,要不就是說「看不懂」、「不知道好在哪裡」(其實常常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意味),要不然就是把村上浪漫化,將自己的心情故事投射到村上的文字中。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我認為,不是因為台灣社會缺乏疏離感,而或許是這種疏離感遭受更大的壓制、被潛抑的更深,說不定用其他更糟的方式(而不是用文字創作的方式)表現在我們社會 中。 先前在網路森林中,您談到關於漂流旅行(以及得到救贖的可能),關於deja vu,關於旋轉木馬,關於村上作品中的時間跳躍,小弟皆覺得十分佩服。過去沒機會提起,趁這次向您致意。 (參考資料:關於「單人領域」部份,參考Michael Balint所著 " Basic Fault " 第五章:「創造的領域」(The Area of Creation)。此書如無意外,將於12月由遠流出版。此書為精神分析的專業書籍,引用實非本意,但我發現除非如此,無法把想說的說清楚。) 一、邊緣人格—持續地不確定,Borderline 昨天讀到Alan Huang 和海豚寫的文字,對於兩人對於疏離、失語、真實與懷疑這樣的議題加以詮釋,覺得很感動。我一直認為應該以精神分析來看村上春樹的作品,才是作為村上讀者通過村上作品找到自我意義的路途。 然而,當我正要坐下來,準備想想該如何針對「疏離與救贖」再說點什麼話的時候,卻乍聽李敖出來參選總統了。李敖要「洗所有台灣人的腦」,「台灣只有兩種人,聰明的台灣人和笨的台灣人」。我覺得,呵呵,很有趣。是只有兩種人,聰明人、笨人、好人、壞人、文化頑童、非文化頑童,不都是同一種人?不都是在系統內的人? 系統,就像一張蒼蠅紙,人人都在裡面,人人都在裡面打電話叩應,洗別人的腦或者提著腦袋等著讓人洗。疏離者之所以失語,與其說不說話,不如說,疏離者與系統隔絕,在自閉的世界裡早已說了無數遍的話,只是系統之外的語言,沒人聽得到,沒人聽得懂。就像電影「沈默的羔羊」,食人魔醫生看著那個嬌小的FBI女幹員說的,待宰的羔羊叫了一整夜,有什麼用?—有什麼用? 這才是我想談村上的作品談到的東西,持續地不確定這個世界的真實性。系統之外究竟有什麼我們是沒看到的,聽不懂的?三毛為什麼蹲在醫院浴室裡上吊?沈默的羔羊為何叫一整夜? 當我看到許多模仿村上文字的作品時,常常問自己,就是這樣的嗎?何以人人都如此確定,我卻無法確定,我們遺漏了什麼?反過來,為什麼只有我確定?為何我又變得確定了? 模仿村上的文字不難,使用簡單的語言和線條、異國的色彩和符號、加上夢與象徵情境、斷片式的敘述。這些其實不太需要學習,因為現代人們不就是如此追求簡單的個人生活?因此只要把耽溺於自我的舒適,像「下著雨,我坐在左岸咖啡館,喝咖啡。」,「抱著貓,聽著爵士樂,望著海洋似的街景」,這樣的文字,就是村上文字了?就會立刻讓人聯想村上春樹了?我無法確定,我們遺漏了什麼?村上春樹洗了大家的腦嗎?每個人都這麼容易就進入了村上的系統了?會不會太容易了一點? borderline,有一條無法確定的界限,無法確定空間的真實與否,無法確定時間沒有一再重疊(deje vu),無法確定精神疾病與痊癒,無法確定壞的自衛機轉(抗拒)與好的自衛機轉(昇華),無法確定男性與女性—邊緣異常人格,究竟,村上春樹所描述的,「我」在女友「島本」的瞳孔裡所見到的「地底的冰河般,堅硬凍結的闇黑空間」是什麼? 我們遺漏了什麼? 想談談Alan huang提到,對我的說法,「現實取用的社會,很難出現疏離者」,感到不解。 疏離是,暫時或永恆,無法進入系統的狀態。無法進入系統是,不完全能或完全不能,產生溝通的狀態。在系統內,也就是蒼蠅紙內,沒有真正的孤獨。 以為使用村上的斷片語言,都市符號,喝咖啡,聽爵士,描寫自己耽溺的情境,就覺得很瀟灑,很孤獨的人,是嗎?不,你仍在蒼蠅紙內,跟你一樣的人,有一、大、把。而且,分不出誰、和、誰、有何不同。 當我們模仿著村上語言,喝咖啡、聽爵士、描寫自己耽溺的情境時,同時發生的有: 某處,抱著小孩,澆上汽油自焚的母親。 某處,一個父親緊擁女兒,全身將自己捆綁鐵絲後跳入河中。 也許我們沒有西方英雄影片裡,一人對抗整個政府陰謀的英雄,一人質疑整個體制的疏離者。但是我們不缺阻絕於社會溝通系統之外的outsider,當整個社會的燈火熄滅,他們走了。他們選擇不再取用社會的一絲一毫,以被社會遺棄者的身分走了。其他的人,於是為了避免這樣的危機,這個現實取用社會的其他的人,就擁擠排隊購買蛋塔,購買kitty貓,爭看無尾熊,擁宋或擁扁,生活無虞的人們從村上春樹的文字菜籃裡,找到時尚語言,寫一篇又一篇模仿村上文字。 關於村上春樹,我們遺漏了什麼? 我閱讀村上春樹時,我感受到的不只是疏離。在黑暗的都會上空,我看到「我」伸出一根指頭,想接觸螢火蟲的一絲光芒。那光芒是如此的微弱,卻是在闇黑的世界裡游移著的唯一光芒。這是我在時報將出版的村上春樹「螢火蟲」裡,以感動誠摯,所翻譯的一段情節。 我想到一個故事。真實的故事。 在台北的一個狹小的公寓裡,大熱天的,一個單親媽媽在廚房裡忙得不可開交,汗流浹背。時間很趕,她快沒時間上班了,廚房裡熱騰騰的,媽媽炒菜炒到一半,才發現醬油用完了。她趕緊跟叫喚六歲兒子,跟他說,買一瓶像這樣,裡面黑黑的瓶子。兒子拿著錢跑去雜貨店,很快就回來了,手上拿著一瓶可口可樂交給她。媽媽一見是可樂不是醬油,氣急攻心,破口大罵,生活慌亂到這種地步,你還不幫忙光會搗蛋!就是你這個不孝的兒子!她口不擇言地罵,我不知道她急怒之下出手打孩子了沒有。 六歲的小孩被罵了,他沒說什麼,聳聳肩,一對眼睛盯著氣急敗壞的媽媽看。如果媽媽知道,如果媽媽不是忙壞了,她可能會想到在兒子的小小心靈中,兒子手抓著錢跑到雜貨店,他看到冰箱裡的可口可樂,想到汗流浹背的母親,他毫不猶豫地便將手上的錢換了冰涼的可樂…… 自己的語言,即便是無聲的語言,自己的語言。 那六歲小孩與母親的那一瞬間的關係,是一種暫時的疏離狀態,孩子想表達的溝通不全症候語言,是一種疏離的語言。但是,我不知道,即便在這種疏離的狀態中,我看到了一種救贖的可能,一種感動。像這樣的真實故事,存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周圍。 也許這是我們對於村上春樹所遺漏的部份。 我期待看到使用村上文字的作者,不再在符號上打轉,不再耽溺於速成的安逸享樂。 讓我們說出自己的語言,即便是無聲的語言,自己的語言。 假設文字寫手村上春樹有一條裸露出來的神經,那神經與某些特別的人相接觸。再接觸的過程中一種感動被激發,一條來自系統的神經偶然接觸了外界,一條原本為偵測人心的扭曲可以到如何程度的神經,到頭來變成一種祝福,成為疏離者的守護天使。成為銷售數百萬冊的作品,成為許多讀者耽於閱讀的書籍,成為許多作者刻意模仿的文本。 這條裸露的神經,在某種程度上,來自於村上本身的生命經驗,他的成長,他的喜悅,他的創傷,他的意義,他的詮釋。這一切都是他的,是村上春樹這樣的作者的張力,寫出讓人感動的文類。 模仿村上文字的作者應該如此自許,只要是人類,都有一條裸露在外的神經,一條自己必須負責,也唯有自己才能解釋其意義的神經。如果使用村上春樹的語法,只是為了自己貧乏的生活增加流行品味,就像來到山地部落,戴上羽飾,穿上鹿皮靴,照一張相,可是沒有人會因為看到相片而被你矇騙,為什麼?你沒有部落民族的眼神。作為村上文字的寫作者,抓住的應該是自己的脈動,自己的語言。 我們可以把村上春樹當成一種流行語言,出CD,出印有村上的汗衫,把自己的名字取為羊男或什麼老鼠之類的,村上本身卻永遠是村上,就像你永遠是你,我永遠是我,每個人都應仔細檢視自己生命裡所裸露的那條神經。當我們的閱讀隨著村上的「我」那雙眼睛梭巡著村上所看到的世界,那個經由村上的經驗所達到的世界感,並不是我們的,我們的世界感在於我們自身的成長經驗,喜悅、成功、憂傷、痛苦、挫折,屬於世上唯一無二的我們自己。最後,我想要講的是,抱著貓、煮義大利麵、喝咖啡、聽爵士樂、看著院子裡的樟樹,羊男、海豚、學習使用這些城市符號之時,不要忘了自己的特殊性,不要被想像的符號感動,被自己的真實故事感動。 我自己也在做這樣的努力。 Evany,很謝謝你又為我寄來這麼多的資料。這二天,山姆颱風的影響遠離。我所居住的、濱海的山城的天空又恢復初秋的爽朗清澈,藍得遼闊。在這樣的時候,在一個有風吹的窗口寫信給你,或許也算是人間的一種幸福吧! 關於疏離感,尤其是村上文學所亟欲表達的現代都市消費文明所衍生而出的「疏離感」,很抱歉,如你所知,我對村上小說涉獵實在不足,所以恐怕無法多說。唯一能說說的,也就是我所知道的「疏離感」或「異化」(Alienation,我不曉得網路森林中大家所熱烈討論的是否就是這個東西?) Alienation的普遍定義 「疏離感」或「異化」這個名詞純粹是西方產物,最早常被用在財產讓渡與贈與之中,後來由於馬克斯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將之應用到分析資本主義勞動過程,因而慢慢產生特殊意涵。到了今天,「疏離感」幾乎已成為分析現代生活最常見的名詞了(還記得雪歌妮薇佛所主演的《異形》嗎?英文片名Alien就與此有關)。而實際上其概念還是很模糊、意義也很含混。以大家比較容易找到的《簡明版大英百科全書》為例,它便為這個名詞下了 6 個定義︰
關於自我異化 這些定義,前 5 種都很好理解,較難說清楚的是第 6 種的「自我疏遠」或「自我異化」。關於這點,同樣有一籮筐的學說定義,包括馬克斯、涂爾幹、韋伯、存在主義、新馬克斯主義……等等。為了省時省事,我只舉最原始的「馬克斯理論」,跟我很主觀認為,或許與村上文學較有關係的「存在主義」來說明。 按照馬克斯的說法,資本主義下的勞動是「自我異化」的根源︰勞動不是自發的,也不具有創造性,而是被迫的。勞動者不能控制勞動過程;勞動產品被別人奪去並用來反對勞動者;而勞動者自己反而成為勞動市場的商品,「自我異化」因此便產生了。用比較簡單的說法,資本主義下的勞動者是龐大機器下的一顆小小螺絲釘,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成為機器的一部份,每天轉個不停,卻永遠不清楚自己所製造出來的是什麼?也享用不起自己所製造出來的產品。並且一旦機器翻修,還可能毫無道理地被抽換變賣。在這種情形下,身為螺絲者自然逐漸與自我疏遠,搞不清楚自己存在的意義與目的了。 而存在主義的看法呢?多多少少也與馬克斯觀點有些關連,不過將對象擺置到整個人生情境之下來說明。以沙特而言,他對於「自我異化」的說法是︰「在一個失去意義、失去目的的世界裡,一切事物的自然狀態」(大家是否已嗅到村上那棵春樹的一絲味道了呢?)。至於世界為何會失去意義、目的?其根源則在於尼采所說的那一句「上帝死了,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許的。」換句話說,由於工業文明的擴展,宗教日漸自個人思想領域退縮,人們固然因此得到了自由,但同時也必須承擔起沒有上帝的全部後果。這些後果就是「被棄」、「焦慮」和「絕望」。 所謂「被棄」,是指上帝死了,人們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依賴的,「存在先於本質」,人就是在那裡了,他的存在根本沒有原因、理由可以解釋。以《世界盡頭與冷酷異境》一書為例(很抱歉,這是我唯一仔細看完的村上小說。我看的是賴明珠譯本,可是不覺得「世界末日」譯法是恰當的,所以改成這樣),「我」的來歷,我們一無所知(其實也一點都不重要)。我們唯一能知道、必須知道的是,在「我」還來不及說「不」的時候,他的腦部早已被改造過、被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力量給宰制住了。 至於「焦慮」,則是指人的狀態,因為即使人是「被棄」在這個世界上,註定要孤獨過完這一生。然而無論說「是」或說「不」,人畢竟還是可以選擇的,而只要選擇便有責任,伴隨責任而來的就是「焦慮」。只是這樣的「焦慮」,不但不會構成行動的阻礙,反而是促使人們行動的條件----人的下一個選擇是基於上一個焦慮而來的。--「我」在《世》書中不斷的奔逐追趕,闖過一關又一關,其本質便不無「選擇/責任/焦慮/行動→再選擇/再責任/再焦慮/再行動→……」的味道在內。 最後談到「絕望」。它的意思是,儘管我們因焦慮而選擇,因選擇而有行動。可是基於「被棄」的這個本質,人們所能控制及影響的的幅度其實極為有限。就算是我們有所選擇,敢於行動,其結果終究還是個未知數。這個特質,或許也就是《世》一書,所以讓人深覺懸宕、讀不釋手的原因: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我」,面對這麼龐大的體制跟四處埋伏的危機,東衝西撞的結果到底會是什麼?沙特曾說過︰「人除了他意圖怎樣之外,就一無所有,只有他體現自己的時候,他才存在。因此,他除了行動的總和之外,就一無所有;除了生命之外,就一無所有」,《世界盡頭與冷酷異境》的蒼涼或深刻所在,就我很主觀的看法,完全體現在「我」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動,尤其是全書最後毅然拒絕說「不」的那個雄渾的手勢。因了這些行動,「我」方能完成自己的生命----作為價值根源上帝死了,人的選擇/行動創造了一切。 台灣情境 一下子說了這麼多,大概早讓你聽得迷迷糊糊了。其實,我的用意不過是想說明,「疏離感」一詞,無論在社會學、哲學乃至文學上,其內涵存有很多不同層次與紛雜的定義,當然也就會以不同的情境出現在不同文化脈絡、社會結構乃至不同時期的個人生命之中。也因此,在還沒有下過定義,說明其內涵之時,就斷言「華人社會缺乏某些東西……,就是疏離感。」,這似乎有些大意且大膽了。甚至,如果你願意換個角度逆向思索,讓「村上春樹文字很容易流於自我陷溺的通俗愛情故事和美食文化主義象徵」的背後原因,在某種程度上,我很主觀的理解,也可以解釋成是另一種「非自覺式的疏離感」(被資本主義馴化的、喪失創造力的、鸚鵡學舌式的)有以致之呢。 所以說嘍,我的看法很簡單,一如有「中心」就有「邊陲」,有「體制」當然就會產生「疏離」。誠如alan所言,台灣與日本社會結構不同,疏離感的產生當然也會不同。台灣近四十年來最侵犯個人的體制在於「戒嚴」一事,所有明顯的疏離感自然也就圍繞著政治體制不斷地在發生著……。像「西方英雄影片裡,一人對抗整個政府陰謀的英雄,一人質疑整個體制的疏離者」或許也必須從這裡去搜尋才能找得到--鄭南榕、詹益樺、吳耀忠、施明正等這些已經消逝了的生命;施明德、李敖這兩個依然耀目的人物。典型在夙昔,行動在眼前,在我的看法裡面,其實都是「非常疏離」的疏離者,都是「除了行動的總和之外,就一無所有;除了生命之外,就一無所有」這句話的最佳詮釋者! 再就文學表現而言,以台灣社會的疏離狀態為命題的作家,同樣不乏其人。在此或許可以舉本身便與今日台灣政治深度疏離的陳映真先生為例,從早年的《第一件差事》、《將軍族》起,他的作品便始終充滿著荒蕪與疏離。最具代表性的兩篇作品「山路」跟「趙南棟」,更是將因為政治體制的荒謬與資本主義的侵蝕,使得個人生命完全失去意義與目的的情境表露無遺。「山路」的女主角蔡千惠甚至為了驚醒於「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而「終於在醫學所無法解釋的緩慢的衰竭中死去」;出生在看守所、與哥哥相依為命的政治犯么子趙南棟則成了一個「讓自己身體帶著過活的。身體要吃,他們吃;要穿,他們就穿;要高興、快樂,不要憂愁,他們就去高興,去找樂子,就不要憂愁……身體要make love,and they make love……有什麼欲求,就毫不,毫不以為羞恥地表現他們的欲求。他們用他們的眼睛,心意和行動,清楚明白地,一點也不會不好意思地說,我要,我要!」這樣的一個人(如此的趙南棟,其特質,似乎跟村上筆下的某些人物有些相近之處);另一篇喜劇似的沈重小說則是張大春的《四喜憂國》,離鄉背井在社會底層苟活的老兵四喜,最後無法接受沈重的現實負擔與時空變換,竟然天天撰寫「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到處投稿,相信報紙「多登文告,少登壞事、壞消息,大家都不會學壞了,全國軍民同胞們,解救同胞,光復大陸,讓子子孫孫都能過好日子,這就對了」……。 真是抱歉,半抄半寫,沒想到竟是落落長、一大堆。我很懷疑,這樣的一封信到底能發揮多少「對話」的功用?遠居山村的人,於世事一無所知,講了半天,或許都是「言不及義」的贅言也說不定。就像眼前我所看到的這一片清澈的蔚藍天空,在山的那一邊,在你的眼前,或許竟已烏雲密佈、陰暗一片了。所幸的是,每一片烏雲背後都是鑲有金邊的--人的對話與溝通,或許要靠、能靠的就是貫穿這陰晴之間的這道善意的「金邊」吧。請多多保重! MoonFish 1999/8/27 附記,上次被你笑說「MoonMood」拗口難聽,這次改成MoonFish---A fish jumps across the moon,因為我只有養魚,沒有養cow! |
|
|
|
給主編:我來聊天了…… |
|
|
|
 回首頁 |
 關於 |
 評論 |
 創作 |
 感覺 |
 Links |
|
| ~ 村 上 春 樹 ~ | |||||||
|
繪圖: 你有作品要發表? 本站資料內容有誤? 你要提供新資訊? 歡迎利用 Email 與我們聯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