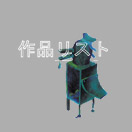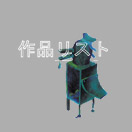|
【森林保護區】--作品解析
(收錄文章 since 網路森林1998∼,著作權屬各創作者所有,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 村上談《挪威的森林》/摘自 1989 年 4 月號《文藝春秋》

為了讀書版的討論,昨天把書和一些資料翻出來看,翻到一篇以前一直沒有好好讀的村上訪談,是1989年4月號《文藝春秋》中的一篇訪問稿,大標題是:「挪威的森林之秘密」。
這篇訪問稿篇幅不短,訪談的當時,正值村上剛從羅馬回國,而《舞.舞.舞》亦出版不久。內容主要是以《挪威的森林》一書為中心,訪談村上的創作活動與想法。雖然這篇訪問記錄,距今已有數年,不過正因如此,倒能看到一些村上當時對於創作的說明。有些基本論題是大家已經知道的,例如村上只是要以「寫實主義」(realism)的手法寫一篇愛情小說。而對於「性」的描寫,也是從這一角度出發,據他說法,當時確實也感受到一些外界壓力,但是也有一些讀者來信肯定他的認真。
其中,談到了如何從「螢」的結尾做延伸,村上自陳思考了很久,漸漸產生阿綠這樣的人物,也就是一個與直子作為對極存在的角色,接著又產生出永澤這樣的奇妙人物。這三人的設定就此完成。
接著,村上說明:關於書中的「我」與直子和阿綠之間,並不是他所謂的三角關係。「『我』與直子的關係,以及『我』與阿綠的關係是平行發展的,不是三角的。」村上說:「真正稱得上三角的是『我』、直子和木漉三人,以及『我』、直子和玲子三人,還有『我』、初美和永澤這三人。這些才是三角關係,因為三個人有一起進行對話。但『我』與直子和『我』與阿綠之間是互相平行的。」
村上進而認為平行式的關係與對話是比較容易的寫法:「在《聽風的歌》裡完全沒有出現三角關係,全部都是一對一的關係。所以在對話上,都沒有三人談話。」關於《1973年的彈珠玩具》中的「我」與雙胞胎,村上認為也並非正確意義下的三人,因為雙胞胎是分裂開來的同一個人格。
村上說:「之所以會這樣也是因為我都沒有為人物取名字的緣故,在三人對話的時候,登場人物是不能沒有名字的。」村上因為不為人物取名字,也因此下了一番功夫:「一直到《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為止,我都沒有替登場人物取名字。有些是用職業名稱,例如司機啦。至於J(中譯為「傑」),是因為經營爵士酒吧
(jazz bar) ,所以就稱做J。這些都是像記號一樣的東西。
「為登場人物取名字使我非常高興,終於能夠寫三人對話了。《挪威的森林》裡三人對話特別多,就是因為我太高興了,因為獲得了新的關係。」村上自認那種描寫一對一關係的手法,到了《尋羊冒險記》已成陳規,所以也想要突破。「我第一次取名字是在短篇集《麵包屋再襲擊》中,其中出現了渡邊昇這個名字。有了名字之後就可以寫三人談話,也可以寫更擴展的對話,要所謂『寫實主義』也可以了。」
至於問到究竟為什麼不取名字,村上只模糊地說:「這一點我也很難說明,對於取名字覺得有點害羞吧。」經詢問之後,村上仍說:「嗯,就是有點害羞。例如卡夫卡都用K吧,我在心情上有點瞭解他為什麼這樣。」
「哎,也有人已經知道了」村上接著說明:「渡邊昇這個名字其實是插畫家安西水丸的本名。有一次聽到有人問安西水丸本名叫什麼,他回答『渡邊昇啦』。那時候,覺得有點新鮮,哦,這個人叫渡邊昇啊,我的腦袋卻又輸入那個人的名字是叫安西水丸,結果突然覺得『我是渡邊昇』這樣說很新鮮。這種記號上的新鮮喜悅感,從此就被裝在『渡邊昇』這名字中了。」
村上一直強調《挪威的森林》是他所謂的「寫實主義」小說,這裡的「寫實主義」,在他看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關於這一點,村上在訪談中,也有一段說明。
「所謂寫實主義小說,並不是就把現實的事情真實地寫下來。事情是否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使人在閱讀的時候感到很自然。寫的東西也許其實不是自然的,但是如果能讓人讀起來覺得很自然,就是寫實主義。反過來說,雖然寫的是真實的東西,但是讀起來卻不自然,就不是寫實主義。這是我對寫實主義的定義。」村上認為,就《挪威的森林》而言,也正是如此。如果以很仔細的眼光去探究此書中的事物,或者是拿到那個時代底下去看,會發現充滿不真實或不自然的地方。但是,除非真的是很拘謹的人,要不然讀起來大體上應該會覺得相當自然。
「事情是否真實,並不是必要的;看起來自然才是重要的。就拿電影來說吧,」村上比喻說明;「科幻電影中的星星,都是在宇宙中一閃一閃的,星星究竟是怎樣,我們看不見。但是,閃耀的星星,在電影的宇宙中看起來卻是寫實的。我所謂的寫實主義便是這個意思。」
讀者對於書中的人物是否真正存在,常感到很好奇,但村上認為真實與寫實是不同的。例如令讀者感興趣的「突擊隊」聽收音機作早操一事,是確有其人其事(後來成為一名模特兒,但村上並未和其再有聯絡)。不過,據村上說明,實際的突擊隊是一個正直的人,而並非讀者所以為的那麼有趣。村上也接著說明,關於作品中人物,其實都是由作者所組合塑造的。「以這種意思來看,倒不如說我書中的人物,不論男女都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不是我自己吧。」
訪談中,關於故事人物結局的生與死,村上也談了一些。「結局誰會活著誰會死去,我在寫的時候並不知道,完全是以寫實主義的方式寫著。」村上道:「說起來,《挪威的森林》這本書要讓誰活著或要讓誰死去都是非常困難的,最後應該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然而,在寫的途中有時還是會困擾,會考慮究竟這樣作好不好。但是這些困擾,在那個時候認為應該是怎麼樣,就會照那樣作結。當然,這只是對我自己而言,別人說不定認為不是這樣吧。」
就直子與阿綠兩個主線而言,讀者也許認為直子已經死了,而阿綠還活著,村上卻說:「我與直子如今在事實上還沒結束,開頭的部分其實就提示了這一點。」接著他又說:「其實我也曾經想過,反過來讓阿綠死去。阿綠並不是不會自殺的類型。但我想的是,讓她死去是比較好的嗎?」村上便曾考慮過,如果失去了阿綠,對於書中的『我』一開始那種不理會世界的性情而言,會成為怎麼樣的情形。
「但是,這樣一面寫一面思考著可能性,事物的發展方向有時會馬上改變掉。」村上說。
接著問到關於最後玲子自療養院出來,並與「我」上床的段落,村上亦覺得是很自然的。「我覺得不這樣是不行的。這在寫作手法上是類似情感淨化
(catharsis) 的效果,不過我最初倒沒想這些。我只是覺得,這樣做是必要的,是比較好的啦。」
接著又談到初美的情形。「關於初美的死,最後的情景是手上纏著繃帶,看她去接電話,然後就走出門。在那個時候,我對於這個人究竟會如何,全然沒有考慮。但是,突然就寫下『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這樣的句子。換句話說,就是忽地一下就寫出來了。」村上接著說明:「這是集中力的問題吧。如果沒有集中的話就寫不出來了。各種記憶也好、心中的各種凹陷也好,要把這些引出來,要在必要的反應下自然地出來吧。」
阿綠是《挪威的森林》中相當有魅力的角色,甚至可能有讀者會猜想,是否與村上的夫人有關。關於這個好奇的問題,村上回答:「這樣想的人確實很多,但是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也許有一些類似的部分,但完全不是同一個人。其實啊,內在方面一點都沒有相似之處,外在看起來也不同。連她也認為是不一樣的。」
但是,村上是怎麼看阿綠的魅力呢?「這個啊,」村上說:「感覺上是象徵著現實的拯救吧。其他的人物,像永澤啦、直子啦、或玲子,所做的都是一點一點地從現實偏離開。但是,阿綠這樣的女子,卻是雙腳踏入現實中生存著,並沒有脫離存在的現實。我想這一點正成為這本小說的力量。而此後,我再也寫不出阿綠這樣的女子了。」村上並再次解釋,阿綠這名角色是綜合而成的人物。
同樣地,也有讀者將渡邊與村上本人等同。「這是相當困擾的。尤其對我而言,一直是寫第一人稱的小說。」村上說:「當然也許是有村上春樹的部分成分,但是畢竟完全是虛構的小說啊。實在是相當困擾。在日本有私小說的傳統,也許有人便將以第一人稱、寫實主義手法寫成的,都視為是私小說吧。」
因為最近比較忙,所以搬運水溝的工作便耽擱了。這篇訪談全長近三十頁,《文藝春秋》又是那種以密密麻麻字體印成的雜誌,以我的能力想要將全文譯出,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過,訪談中有關《挪威的森林》內容的討論,主要便是在這幾段議題上進行的。勉強大家看這樣節錄的片段,實在很抱歉,我想大致就節譯到此告一段落。其他部分亦談到《舞.舞.舞》和《尋羊冒險記》等作品,有些地方我也覺得蠻有意思,如果有機會再想辦法「節錄」一番。
最後,不知道有沒有人特別注意到《挪威的森林》原文書的封面設計:上、下兩冊分別是從封面連到封底的鮮明紅色與綠色。據村上說,這是出版社的原始構想之一,本來是不被採用的。但村上當時覺得這樣強烈的色彩對比,正適合這個情感強烈的故事,所以便堅持採用了這樣的設計。也算是相當有風格的設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