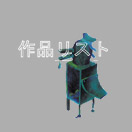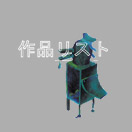|
【森林保護區】--作品解析
(收錄文章 since 網路森林1998∼,著作權屬各創作者所有,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 漂流、記憶、與救贖--村上春樹的《邊境.近境》/李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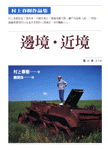
Evany:
漂流與救贖,正是村上春樹近年從疏離到承諾的轉變過程。身為一名長期觀察村上的讀者,我覺得有義務介紹這一部份,也就是除了義大利麵、爵士唱片、咖啡、與幻想之外,想對社會現況盡其義務的村上春樹。
我的寫作也曾歷經一段尋求意義的掙扎,就這方面而言,村上春樹是我的精神導師。
另外,我已答應時報翻譯村上春樹的早期短篇集,希望能提出一種前所未見的乾淨譯文,以饗村上迷。 ∼李友中(《東京漂流物語》作者,新新聞出版)
有一天毫無準備地走出家門,去一個遙遠的地方,停下來看看,不久,又到另一個地方,期間沒有任何關連,只是沿著地圖上的點前進。漂流,結果可能是漂流而去,也可能得到某種救贖,你永遠不知道。你只知道,你要做的是,
漂流旅行。
村上春樹的《邊境.近境》在台北出版,我與專程來台的攝影師松村映三先生在誠品書店有一個對談。村松先生在詳述其黑白攝影集時說了一句話,他的攝影集並不是記錄,而是記憶。這句話正好說明了漂流之旅的定義:「不是探索新知,而是在找出埋藏於深處的記憶。」
找尋似曾相識的感覺,Dejavu。
即使遙遠的國度,走遍千山萬水,漂流旅行者不在增加見聞,而在發現早已在心中隱隱若現的舊臉孔。旅途上一條橋、一棵樹、小巷、廣場、階梯、蜿蜒沒有止境的道路,其實都是漂流旅行者平日夢中的場景。所有相似的感覺、溫度、光線、溼度、老人與小孩的臉孔,山水與雲霧,寂靜的空巷,對親情的嚮往,對偉大的憧憬、對巨大浩瀚空間的嚮往,這些深埋在心中的童年衝動,只是藉著新的路程挖掘出舊的鄉愁。
所謂的鄉愁,似曾相識的感覺,Dejavu。
我問松村映三,他和村上春樹先生如何決定旅行路線?松村先生說,沒有,我們從來不決定。只是有一點,大家都去的觀光據點我們絕對不去,如此而已。
全世界地圖上的所有的景點,其實都毫無變化。從遊覽車魚貫下來的觀光客,照相,購物,迅速回到同族群之內,每一個觀光客對另一個彼此一種阻礙,阻礙了旅愁的可能性。如果你是村上春樹的書迷,和他在觀光景點巧遇的機會,可以說近乎零。他和村上只是在找尋記憶裡,似曾相識的地方。
既視感,(Dejavu︰對於未曾體驗的情境,有以前相似的感覺。)
對松村映三而言,既視感觸發了攝影的意念。這個地方雖然沒有來過,可是多麼熟悉呀!他的《滾滾遼河》黑白攝影集,記錄中國土地上的陌生人,那些臉孔喚起他某種記憶,因而按下快門。
漂流旅行,不僅是自助旅行,而是孤獨之旅。
最近新世代之年輕人開始走遍世界自助旅行。自助旅行者忍受旅行的不便與挫折,不再輕浮聒噪,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性情較沈穩。自助旅行者展現自主出遊的能力界限,難怪大家都說,自助旅行的年輕人有自信得多。
漂流之旅卻不僅如此。
自助旅行者意在增加見聞,走遍幾個國家、去過哪些景點、嚐遍多少美食、看過幾個博物館、多麼懂得生存之道。
漂流旅行者尋找一個能夠安靜凝望的視野,在那地點靜靜抽完一支煙,看看會有什麼事發生(通常是沒有什麼事發生)。
漂流旅行者找尋一種意義,那種意義可能在鄉村,可能在城市,可能在廢墟,或是牆角上的一個記號。
自助旅行者善於規劃路程,熟悉貨幣、地圖、據點、交通、種種旅行技巧。漂流旅行者可能是老人或小孩,空虛的中年人,甚至對生活厭倦的肥胖家庭主婦。跟一般自助旅行者不同,他們不是身強體健的探險者,也不懂求生之道。
不過,真在漂流旅行時,其實那些不是那麼重要。
自助旅行者必須不停移動,看到、摸到、體驗未見的新環境,然後回到出發點。
漂流旅行者不一定回到出發點,可能漂流到無法回頭的地步,無止境地漂流,直到獲得救贖,
或者喪命。
在《阿拉斯加之死》,年輕人克理斯放棄了所有金錢,孤獨走入阿拉斯加的曠野。克理斯看到他父親「萬無一失」的人生計畫成為泡影後,失望地走向無既定路線的漂流之旅。躺在病床的父親,
「……父親的手腳被綁在床邊欄杆上,語無倫次地咆哮,全身直安滿了糞便,他的眼神狂野,一會兒放出挑釁的光芒,一會兒又流露出無法理解的恐懼,眼珠深陷在眼窩裡,清楚地說明了他受折麼的心智狀態,教人心寒。當護士想為他換床單時,他猛烈踢打,反抗施予他的束縛,大聲詛咒他們,詛咒我,詛咒命運。他萬無一失的人生計畫最後把他送來這裡,送到這個夢饜一般的場所。」
克理斯漂流旅行的最後結果是,漂流至不知所終,
喪命。
「……八月十二日,迷失阿拉斯加大地的克理斯在日記上寫下最後的遺言,美麗的小藍莓。接著他爬入母親為他縫製的睡袋,陷入昏迷。他可能死於八月十八日,亦即在他步入曠野的一百一十二天後,在六名阿拉斯加人經過巴士邊,發現他的屍體的十九天前。」
「克理斯最後的行動之一是為自己照了張相片,站在巴士旁,站在浩瀚的阿拉斯加天空下,朝向相機鏡頭,擺出勇敢、快樂的再見姿勢。他的臉憔悴得厲害,幾乎只剩皮包骨,但如果他在生命盡頭曾經憐憫過自己,因為他如此年輕,如此孤獨。因為他的身體辜負了他,他的意志使他失望,由相片上也看不出來。相片中的他微笑著,而他的眼神無疑地流露著:克理斯麥克肯多斯終於如僧侶班平靜地、心如止水底走向上帝的懷中。」
救贖的可能。
村上春樹開始其連續的旅行,他從《遙遠的太鼓》(地中海紀行),《炎天.雨天》(土耳其境內),到《邊境.近境》(墨西哥、外蒙古、神戶等地)。我們會感到奇怪,描寫羊男,鼠,海豚等等幻想作品的小說家為何立意走上長期旅行?
村上春樹曾自述,他無法再繼續描述疏離與孤寂與無望的等待。他必須踏上旅程,詳盡記錄路上的實際見聞。村上開始思索對社會的所有承諾。來到蒙古草原上的烏蘭巴托,其實只是證實了他少年時的想像,日本小學課本中記載日軍與俄軍在烏蘭巴托的戰役。當他走到那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看著遺留在草原上絲毫沒有改變的日軍鋼盔以及毀棄的五十年的坦克:
「那畢竟已經是五十五年前的戰爭了,卻簡直像數年前才發生的一樣,雖然沒有屍體,雖然沒有流血,但卻幾乎處於未經處理未曾移動過的狀態,就那麼散落在我的腳底下。」
村上春樹長期旅行,為了使自己的內在記憶和外在世界的風景不停交錯,提醒自己身在地球的一份存在感。這是村上春樹與心理學者河合隼雄教授對談時,所經常提到的主題--
承諾。
村上春樹不再出現早期小說經常具備的不確定與疏離。村上以實在的文字描述實在的景物,書迷也許無法在他的旅遊紀行看到那種對義大利麵、三明治、咖啡、唱片等近於病態的偏執。村上讀者可能覺得村上的旅遊紀行,抽離現實感的幽默減少了。但那是勢必要減少的,因為找尋現實的過程中的村上春樹勢必慢慢去掉那些,因為他正在一條向承諾與實踐進行的路上。
村上春樹開始花費大量精力撰寫《地下鐵事件》,記錄事件受害者與加害人的心境,探索人性張力的邊境。也許這會令仍迷戀村上早期疏離與奇幻風格的讀者感到失望,然而如果真正了解從安保條約時代反政府的迷惘青年到感受社會承諾必要的小說家,這對村上春樹而言無疑是重大的決定,他曾是一塊漂浮的流冰,現在找到暫時的停留點,他停下來,他必須。
承諾(commitment:自我在心中許下的願望、參與及實踐。)
漂流旅行者尋找這樣的承諾,從每一次的自我甦醒,重新認識自己,開始學習為別人服務。即使是漂流至阿拉斯加的克理斯,一個漂流至不知所終的旅者,他在死前的日記也寫著:
「……現在我覺得自己已經找到安靜而隱密的生活,對善良而不習慣接受他人恩惠的人們有所助益,做些可能有益的事,然後休息、自然、書本、音樂、對鄰人的愛,這是我關於幸福的理想。……(托爾斯泰)說人生中唯一確定的快樂,是為他人而活,他說對了。」
村上春樹說,「……即使在這樣一個邊境已經消失的時代,依然相信自己這個人的心中還是有製造出邊境的地方,而且不斷續確認這樣的想法,也就是旅行,如果沒有這種類似洞察眼力的話,就算去到天涯海角,大概也找不到邊境吧。」
漂流之旅,就像一塊巨大的流冰。緩慢地漂流,在大海中逐漸溶解,發出碎裂的聲音,那也許是漂流旅行者心內的聲音。一種記憶的解放,漂流旅行者來到陌生的境地。
若是漂流旅行者能得到救贖,就會很好,就會暫時停止漂流。
(Post Time: 99/04/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