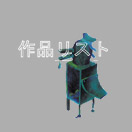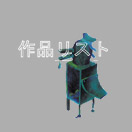|
【森林保護區】--作品解析
(收錄文章 since 網路森林1998∼,著作權屬各創作者所有,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 論《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的空無/Culture(朗天)

一、
最新一本村上春樹中文版作品《天國子民在舞蹈》(博益版)(台灣版叫《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以下簡稱《天》),在二零零零年七月的香港書展會場有售。書收載了六個短篇,都是和神戶地震有關的。這種組合令人想起另一本也是有主題的短篇小說集《萊辛頓幽靈》(簡稱《萊》),不同的是《萊》的主題是孤獨,《天》的主線則是「空無」。
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但難免總會有時感到一種彷彿透自骨髓深處的寂寞。而這種寂寞的來源到最後原來便是「空無」。
一般的心靈空虛是內心不夠東西填塞,又或者填了等如沒填。這裡要說的「空無」不只是東西缺席的結果,不!它反而是可以填塞心靈的東西,它是內容,也是形式──一種存在和生存的方式,一種內裡有「死」,太多「死」的生。
就拿《天》第一個故事「UFO 降落在釧路」為例。它有著典型村上式故事的開端──丈夫忽然要面對一個殘酷事實──妻子不辭而別,而自己實在弄不清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村上曾循這個方向發展出《發條鳥年代記》這麼樣一個長篇,居然意猶未盡,還要一次又一次地寫下去,似乎說明他對自己要作的實驗,還未滿足和滿意。
這次被妻子離棄的男人受同事委託帶一個盒子到北海道去(另一個經典村上橋段!)接待他的同事之妹的女友覺得他很帥,便和他上床(也是十足的村上風格)。然而,在做愛時,男子腦海裡充滿著的只是電視機轉播的神戶地震慘況,因而交合沒法成功。事實上,他的妻子也是在不停看著地震報道畫面後,留字出走的。
字條是這樣寫的:「你的內在沒有任何一件可以給我的東西。……跟你一起生活,就像跟一團空氣住著一樣。」
就在這時,同事妹妹的女友赤裸地伏在男人的胸膛上,告訴了他千里送來的箱子,藏著的其實就是男人的「內容」,他自己不知道,已經交給了別人。
男人悚然,女友隨即補充這只是一個笑話。但,那真是笑話嗎?
故事就這樣完了。這種敘事結構村上在其他短篇小說裡玩過很多次,有趣不在於故事可以怎樣說,這留待研究村上文學技巧的人去整理分析。這裡想強調的是:內裡空空如也的人,不是一開始便空空如也的──不然妻子當初不會和男人一起,更不是不會覺察自己空空如也。
村上要寫的狀況不是空空如也本身,因為內裡沒有甚麼一旦被發覺,內裡便有了新的東西──以沒有甚麼為甚麼的其麼,一種空無。這種空無是可以不停吞噬身體生命力的怪異力量(在《人造衛星情人》中,化為偷走人身體的沒有臉目的人,在《天》的六個故事中,便是作為隱喻的毀滅性地震),是散見於村上作品的「那邊」,是《邊境.近境》裡的「那個」。
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空無」、「那邊」還是「那個」,它們在主體上的「威力」是連帶著主體的覺識而表現的,覺識愈強,威力愈大。對一個無知無覺的人來說,毀掉了便是了,但當事人總來到一個時節,開始察覺有些甚麼不對勁,自己內裡有些甚麼不見了、失落了。起初可能只是隱隱然覺得,後來愈來愈成為自己擺脫不了的魔咒,甚至成了生命的主調了。
村上一直關注的,正是人發覺了這種空無在自己體內之後,跟著怎麼樣的問題。對抗它?順從它?《尋羊冒險記》中老鼠為了對抗,連生命也不要了。短篇「跳舞的小矮人」裡,主角為了對抗,情願不斷逃亡。順從了的人,不是變成《發條鳥年代記》中的綿谷昇,把力量轉移到邪惡的方向,便是被力量直接摧毀,就像被地震摧毀那樣。你愈覺察出空無的存在,它便愈令你難受。因為人的力量和它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唯一面對的方法,最多是盡量拖延,但似乎始終都是要看著自己慢慢成為一具空瞉。
對此,《天》似乎沒有提供甚麼新的答案,但沒有新答案不表示沒有新形式,不少人便認為,《天》可視為村上在
95 年神戶大地震和東京地下鐵事件之後的新創作嘗試。其「新」,究竟在哪裡?
二、
神戶地震和東京地下鐵毒氣事件深深影響了村上,是作者明言,讀者也確認的事實。這本關於地震的小說集,有人認為是自《人造衛星情人》以來,村上春樹創作新方向的展示──他不再只去描寫失去的東西,還不斷去寫以為失去但並沒有失去的東西、不變的東西,以及重新再獲得的東西。這些意見指出,村上似乎是從另一種角度擴大探討生死相關的主題,不再執著於生命中已經失去的東西,而是從全然的空虛中,逆推出活著的意義。(「所謂從死的方法反過來引導出的活法」。──引自《天》中第二個故事「有熨斗的風景」)
以上意見不無道理,但這裡不覺得那是村上作品的新轉向。如果當中真有分別,只是地震和地下鐵事件之後,很多在村上作品中潛在的元素來得更明確外露,而所謂失去和沒有失去,往往只是正面去講和反面去講時表現出來的不同狀況。村上以前也許比較傾向反面去講,地震和地下鐵之後則選擇了正面去講。
正面去講,生命不是缺失了的餘下部分,而是被缺失之源以至缺失本身填滿了的存在。《挪威森林》裡生中的「死」是生活中的一股味道,一種成素,但它還是主要作為「死」來表述的,如朋友忽然死了、失縱了,作用到另一個在生和本來有正常生活的人身上會如何如何。到了《天》,如果還套用這個說法,生中的「死」不再主要以失去來表述,而是透過描寫充滿了「死的生可以怎樣來展現。
你可以說,村上以前的作品,主角大多是身處於失落邊緣或自覺失落之初,並努力對抗生命走向傾斜的人,結局主角的「出路」往往是死抱生息(《舞舞舞吧》),盡量延遲失去一切那一刻的降臨。這種做法非常無可奈何,而且結果不確定,甚至可以說是悲觀的(以《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為最明顯,《挪威的森林》和《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則是向通俗要求妥協,表面上樂觀,深處是難耐的悲涼),《發條鳥年代記》和《人造衛星情人》結局變得樂觀,固然是村上對於「出路」,終於掌握了他接受的表述方式,但若要視為今天作品的過渡,似乎也無不可。這過渡便是把故事主角的主要狀況轉為完全陷身失落之中,像《天》的一眾主角,像《電視人》收入的短篇「睡」的家庭主婦,像《人造衛星情人》中小瑾的情人。他們都是生不如死的人,村上的新嘗試也許是要在他們身上確認出一點生存意義。
朗天來自香港 2000 年 8 月 2 日
(Post Time: 2000/08/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