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序
衣服有如人的僮僕
.楊澤
1.
A‧賀胥黎,英國小說家,《美麗新世界》作者,這是眾人熟悉的。他也是較早接受迷幻藥(麥司卡林)實驗的西方文人,寫了《眾妙之門》一書,描寫第一手經驗,這就少有人知了。但,更不為人知的也許適,賀胥黎在談論迷幻藥物時,一度談到衣服和衣服的「戲劇性」,有底下一段看似荒唐的「自問字答」: 服用麥司卡林藥丸的人和藝術家無異,對他來說,衣服乃是有生命的象形文字,代表了「存有」的獨特、純粹和神秘。我那件法蘭絨灰長褲的皺褶,甚至比椅子─雖然也許比不上瓶中那些徹底超自然的花朵──更加充滿了「本然」。我的灰長褲的皺褶,它的「恩寵」狀態的背後會是什麼呢?我說不出來。也許因為,有褶層的衣服不單形式奇異,而且富戲劇性……它阿容光和奇妙,完全屬於另一種層次,甚至最高的藝術亦無法表達。 法蘭絨長褲,所謂 flanel,今天已經不流行了。它過去是英國貴族打板求的穿著,直到 5、60 年代,仍然適某種身份、地位的象徵──這也是為什麼 弦,在也許適他最迷人的一首詩《如歌的行板》中寫道:「晚報之必要/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姑母遺產繼承之必要……」。法蘭絨有種美妙的觸感,在賀胥黎看來,透過藥物實驗或藝術家的眼光──兩者在他心中一般神聖──日常的法蘭絨長褲也可充滿「靈光」──可拿來和波提切利、塞尚的畫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賀胥黎頻頻使用了「存有」、「本然」不少抽象字眼,把一件衣服的感官表面、美感形式說得「神乎其神」,這有可能是因為他當時處在藥物狀態裡,但今天看來,躲在那些頗唯新的詞彙底下,不排除有屬於 Fetishism(「敗物教」、「戀物狂」)的東西在。 弦,在也許適他最迷人的一首詩《如歌的行板》中寫道:「晚報之必要/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姑母遺產繼承之必要……」。法蘭絨有種美妙的觸感,在賀胥黎看來,透過藥物實驗或藝術家的眼光──兩者在他心中一般神聖──日常的法蘭絨長褲也可充滿「靈光」──可拿來和波提切利、塞尚的畫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賀胥黎頻頻使用了「存有」、「本然」不少抽象字眼,把一件衣服的感官表面、美感形式說得「神乎其神」,這有可能是因為他當時處在藥物狀態裡,但今天看來,躲在那些頗唯新的詞彙底下,不排除有屬於 Fetishism(「敗物教」、「戀物狂」)的東西在。
張愛玲也說過,衣服是一種「袖珍戲劇」/如果說賀胥黎在法蘭絨長褲上發現的是,畫一般凝止了的「永恆瞬間」──某種幽微的戲劇敢──那麼,張愛玲則把衣服當道具,自顧自地演起戲來。
張愛玲喜歡研究服裝,看巴黎時裝雜誌,而且自己設計帶有前朝遺風,摩登而豔異的服裝。她從小沈迷在藍綠、湖綠、孔雀綠、桃紅、鵝黃等極盡幻想能事的配色,20 歲上下寫出中國最早一篇服裝評論的長文,〈更衣記〉。在照片中,我們看到她穿銀狐小襖,翻出旗袍的高領子,有一種她深以為傲的「華麗」──有人會說是「俗豔」或「妖氣」。她其實既世故,又天真。陳若曦說,張愛玲「像民國二十年代學堂裡的女學生」;她的人不夠開朗,因此所形成的身體和服裝之間的對話,亦發加強這種帶有自閉傾向的「魔幻」。
我們今天已經察覺到,張愛玲的生活和藝術是連續的,她的服裝和寫作,皆有高度的自戀成分在。張對此,一向有自知之明。她早覺得「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袖珍戲劇」云云,乃是告白,某種張愛玲式的「私語」: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語言,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這樣地生活在自製的戲劇氣氛裡,豈不成了」套中人」麼?(契訶夫的「套中人」,永遠穿著雨衣,打著傘,嚴肅的遮住他自己,連他的錶也有錶袋,什麼都有個套子) 猶如這裡所說的契訶夫式「套中人」,張愛玲的寫作使我聯想到「中國套盒」的裝置。無一例外,張愛玲的人物都在自製的服裝冊中,不斷換穿一套又一套的情節(如同少女所喜愛的紙娃娃遊戲);衣服的故事和人物的故事疊在一起,而前者往往蓋過了後者。衣服不單是自戀、自愛的展示──人物的「語言」(所謂「千言萬語、欲語還羞」)也就從衣服的褶層中流洩而出──衣服其實是多少帶有自閉、失語傾向的人物的內在迴聲,一種奇特的「自言自語」的景象。終其餘生,張愛玲是一個不喜與人街、少語言的人;她的人生何嘗不是,一頁頁鑲嵌在衣櫃裡的「無言劇」。
2.
衣服既是孤獨的遊戲,也是眾人的遊戲。一個人在人群中跳舞,總希望光打到他身上,至於光是打哪來的,還是從自己的衣著、打扮散發出來的,那並不重要。衣著的扮演,既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又是極其自我的想向與模擬,但主觀、客觀不斷挪移的結果是,兩者之間有份張力,界線卻是一貫的模糊、曖昧。這種模糊曖昧讓人可以充分享受到,自我隱藏與張揚相互撕咬的快感;更重要的是,再看與被看之間,在誘引與抗拒之間,你我可以驅使身上的衣服去做,至少,底下幾件事──說話、跳舞、示愛;然後去真正有所行動。想到衣服的奇妙時,我想到的是雙人舞,是 2,而不是 1,不是單人舞。一般說來,中國人喜談「吃」,很少談「穿」。說到前者,每人都隱隱的亢奮,所謂「津津樂道」是也,卻少見人談後者,談得神情飛揚。但偶然,我聽到有人這樣說:「我永遠記得 20 歲,第一次穿旗袍的感覺──那是連身及膝,一襲有小開叉的短旗袍,因為旗袍的領口用小勾勾扣住,因為它合身的方式是緊貼住你整個身體的線條,穿上旗袍那刻的感覺是,有一個陌生的男人正溫柔地、緊緊地抱著我……」
「我當時還不懂得,衣服和自己的身體,也有跳舞時所謂 lead And follow,領導和跟隨的竅門,只覺得,旗袍緊身的程度深深影響一個女人的行動,坐下時尤其明顯。你的舉止,你的manner,變得緊張、可笑──你意外地發現,你的脖子拉直,背是挺的,雙腳幾乎自動併攏,自然而然會有一種你平常完全不熟悉的、矜持的姿態出現……」
整個 80 年代,我住紐約;固定冬天要下好幾場雪,雪若稍大一些,就字人行道結成薄冰,風吹過,空氣中的冷冽使行人縮成一團,我也不例外。我把自己深埋在衣見開什米爾短大衣裡──那是我用 20 塊美金,不多不少,從東村街角一個年輕黑人手上買來的,也是我所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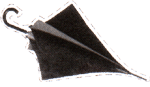 有的第一件真正拿來禦寒的大衣。我通常先穿外套,加一條長圍巾,套上大衣再出門;開什米爾如此溫暖、輕柔,一點也不笨重,不顯舊,我在路上走著,慶幸自己眼光好,第一眼在地攤上就看到、買到它,不必像其他人穿球一般腫脹的羽絨夾克,在路上滾來滾去。想到這裡,步伐亦發輕快起來;甚至偷偷希望雪再下多些,天氣更冷、更凍,好讓我帥氣地出現在外國情人面前,分享它帶給我的幸運和光榮。 有的第一件真正拿來禦寒的大衣。我通常先穿外套,加一條長圍巾,套上大衣再出門;開什米爾如此溫暖、輕柔,一點也不笨重,不顯舊,我在路上走著,慶幸自己眼光好,第一眼在地攤上就看到、買到它,不必像其他人穿球一般腫脹的羽絨夾克,在路上滾來滾去。想到這裡,步伐亦發輕快起來;甚至偷偷希望雪再下多些,天氣更冷、更凍,好讓我帥氣地出現在外國情人面前,分享它帶給我的幸運和光榮。
衣服有如人的僮僕或親信。它代表著人的第二個自己,為自己去進行各樣秘密的任務。忠誠、牢靠,它不僅聽你使喚,幫趁必要的場面,甚至型塑你的儀態,校正你的身體──如開什米爾為我所做的──烘托你益發有主人的身價和派頭。童話<國王的新衣>講的,其實是一個眾叛親離的故事:國王被魔鬼愚弄,以致連衣服,他最貼身的親信,都背叛了他。大家應該同意,在自我的王國裡,性愛是最浪漫的騎士;而在騎士的封地上,衣著舉止則是最忠實、最受器重的扈從。耐看經穿,穿起來書適自在的衣服逐漸變成一個人「皮膚的」延伸自我的一部份。久而久之,等你驀然回頭,它還在那裡守候著你的注視,時間只顯得它更富耐心、更有「型」,自然而然地散出一種光澤來。
如果說衣服像男人的親信,對女人而言,它更像情人,或腹語術裡的傀儡。我記得安東尼‧霍普金斯演過的一部片,《傀儡殺手》。片中,霍普金斯是一個在夜總會表演腹語術的藝人,因為隱藏的殺機,最後竟由它的傀儡代他出手,殺了人。情場如戰場,一幅不單是女人手上閃閃發亮的暗器,也是那攜暗器殺人的傀儡,她意識的代言人。張愛玲說,「各人住在各人衣服裡」;然而,在情愛的遊戲裡,當兩人相對、四目交接,女人往往覺得,保護自己的最好策略就是主動攻擊──於是在各種場合,輪流派她各式各樣的傀儡上場,希望可以一招致對方於死地。
3.
傀儡會使壞,這是女人深知的。好萊塢明星,梅蕙絲說過的那句妙語:「當我好的時候,我是很好;但當我壞的時候,我更棒。」(When I am Good, I am really good; but when I am bad, I am better.)傀儡讓好女人變壞,變成所謂的「壞女人」,這是為他們好。(張愛玲也說過,正經女人雖痛恨蕩婦,若有機會自己扮,沒有一個不躍躍欲試的)然而,傀儡技士女人身體裡的惡魔,不排除反過來成為女人的主宰,她的惡魔情人,對她做出種種命令和要求,溫柔且殘暴,整個人類服飾史遂充滿了束腹、束胸、玉手、小腳,諸如此類,為了建構完美的陰性氣質而進行的「人體改造」。
各時代都有其審美標準和人體典範,在全然相對的標準下,你我實無從怎樣多反對或多贊一詞。人體改造有徹底病態的一面、中庸的一面;激進的一面、保守的一面;但最主要的,是它的「虐與被虐」的情境與源源不斷的快感。法國思想家福柯認為,你我的身體是聽話的、服從的身體,受限於社會對個體的種種控制和塑造。但,人的自我又是複雜而矛盾的混合體,永遠在快樂與痛苦、馴服與反叛之間擺動。以中文為例,衣服的「服」本來就有」聽從」的延伸義,代表約束的形式與力量,可見於「服從」、「服務」「馴服」等字眼。在我看來,性愛既是人類服裝史的一大動力──人體的政治、性愛的政治、以及衣飾的政治,其實是三位一體。
蔡淑玲最近在談波特萊爾時提醒我們:「知識是一種『錶框』;意在『媾合』各式出口──如『婊』;意在尋求各式典範──如『表』。」我無意在字源學裡做文章,但在蔡所說的知識框架、典範的問題外,我覺得可以加上「外表」以及「表演」的說法,點名感性表面和身體、扮演的主題。現代人的衣服強調簡潔、講究理性的線條與結構,卻又傾向無限制的幻想、遊戲、機智與曖昧性。不過,如果忘了,把身體和扮演的觀念加進來,那麼,大部份的服裝評論──包括張愛玲和羅蘭‧巴特──難免淪為形式的遊戲、美麗的修辭。副刊上的服裝評論常見這種「空口說白話」的現象──到頭來,只會是消費、購物的不斷反射,只能發展成一種依賴擬像、徹底魅俗的人生態度。
在我看來,身體和衣服之間有極多對話可能;比較淺顯,但也頗動人的,還要算是那層 lead and follow ,待與跟的關係。身體與衣服有如男、女舞伴;跳雙人舞時,男人得表明他的舞步,有效地引導前進,這樣女人才會滋生信心,跟著男的移動;反過來說,女方也需保持輕鬆,才能自然跟隨男人的引導。領導與跟隨之間,其實是一種信任的問題;到最後,男人與女人,帶 與跟,猶如機器般自然運轉,雙方「化有招於無招」,水乳交融。不錯,就像女人可以反過來引導男人,衣服也可以太過形式和想像力,啟發、訓練我們。我想到的是,好萊塢片中慣見的,一個男人或女人,捧著一件宛如「神蹟」搬的衣服,抱著它翩翩起舞。半是真,半是假;半是神聖,半是瘋狂;半是遊戲,半是深情──自我的界線如連一般不斷擴張與回歸,在旋轉中展現出自我純真的姿態與風格。 與跟,猶如機器般自然運轉,雙方「化有招於無招」,水乳交融。不錯,就像女人可以反過來引導男人,衣服也可以太過形式和想像力,啟發、訓練我們。我想到的是,好萊塢片中慣見的,一個男人或女人,捧著一件宛如「神蹟」搬的衣服,抱著它翩翩起舞。半是真,半是假;半是神聖,半是瘋狂;半是遊戲,半是深情──自我的界線如連一般不斷擴張與回歸,在旋轉中展現出自我純真的姿態與風格。
怕男人/女人、僮僕/情人的二分法引起誤解,我得說,他們中間有相當大的灰色地帶。陰性化的男人、男同志是馬上可以想到的,當然,還有西方服裝史上舉足輕重的 dandy,勉強可翻成「紈褲子」或「時髦兒」。Danny 處在上流社會的外圍,容易遭側目以對,如波特萊爾、王爾德等人,都是以悲劇收場。魯迅說:王爾德遺照,盤花鈕釦,鑲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見猶憐……」。F‧哈里斯是王爾德的好友,也是他的傳記作者,他提到王爾德出獄前,非常拮据,透過另一密友懇請哈里斯給他做些衣服。哈里斯找到王爾德的裁縫,預定了兩套衣服,但裁縫拒絕接受預定,不願給王爾德做衣服;哈里斯派人送現金去,才把衣服做好。哈里斯把衣服寄去給獄中的奧斯卡,後者的感激可以想見。雖說有人會覺得不可思議──人在牢獄裡如此大費周章──對王爾德而言,確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炭」在這裡多了一層精神的意義:也就是說,衣服已不僅是衣服,而是一種自我的表徵,沒有它,王爾德即使人在獄中,亦寸步難行!事實上,dandy 所代表的,不僅是風格化了的生活美學,而是一種生存哲學或「自我倫理」。福柯認為,dandy 是一種現代英雄;這是因為 dandy 對轉瞬即逝的都會情境有悲劇性的理解,同時永有一種擺盪於主流文化邊緣的探索態度:他不追求自我本質,而是在尋找、實驗一種新自我的可能。可以想見,這種新自我的可能,是要以身體作為重大代價的。
|